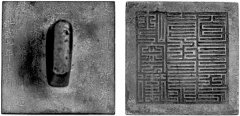皇太极文化形象塑造
历史上,每种文化体系的核心,是群体成员理解和认同该文化的价值观念及与之相配套的行为准则,也是明确自身政治、社会归属的关键。若用此理论解释历史上的王朝建构,每位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以及皇权天授的帝王都是其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随着他们在所处文化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他们便掌握了文化与政治的话语权,借此实现利用文化符号来维系王朝统治的目的。他们确立自己文化核心的方式既可以是多面的帝王形象塑造,也可以通过整合文化体系来实现。
满洲与蒙古之间的政治盟姻、经济往来与文化互动,使得“蒙古元素”“蒙古情感”在满洲社会中无处不在,二者统一且互为表里。皇太极时期,满族问鼎中原的时机尚未成熟,与蒙古的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因此,其积极投身仪式表演和概念性仪式阐释,为随后蒙古成为清王朝域内的一部分,以及形成清王朝独具特色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蒙古情感”的国策彰显
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密宗与西藏苯教结合而产生的宗教,但是,藏传佛教中丰富的仪轨、医术、历算却是萨满教不具备的。因此,藏传佛教以其内涵丰富的宗教哲理和隆重的仪式,更能吸引或满足满洲统治者精神上的需求。1635年,皇太极征服察哈尔部后,墨尔根喇嘛将藏传佛教护法神嘛哈噶喇铜像送至盛京。皇太极以嘛哈噶喇所具有的重大象征意义,于崇德元年(1636),特敕建“实胜寺”以供奉。崇德四年正月初三,皇太极又于新年率和硕亲王以下宗室王公,前往实胜寺,向嘛哈噶喇佛像行九跪九叩礼,皇太极此举表明新年礼佛已纳入清王朝国家祭祀礼仪体系当中。这既是满洲敬重蒙古诸部民众的宗教、文化传统的体现,也是向蒙古诸部昭示清王朝的“天命”所归。
借鉴蒙古“长生天”信仰
对天地立誓是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信仰——萨满教中最为突出的宗教仪式。在萨满教中最高的神祇就是天地之神,游牧民族的历代统治者均认为皇权是上天赐予的,所以,他们会以宰杀白马祭天、宰杀黑牛祭地这样最高规格的仪式来表达对天地的崇敬。这即是萨满文化中的“天命观”。刘小萌指出:满洲所提“天”的观念同样借自蒙古,是在满洲传统中有“天神”的观念的基础上,按照蒙古“长生天”的信仰模式来举行向天祈祷的仪式。清初,举凡将士出征或者凯旋,与蒙古订立联盟等国家军政大事,清朝统治者都会举行祭祀天地习俗,宰杀白马、黑牛祭祀天地,以示隆重。让崇敬的天、地之神知晓双方的诚意,并保佑遵守盟约或者惩罚背弃盟约的一方。立誓双方需恪守承诺,不可背叛对方,利用信仰的力量来保证彼此之间的信任,以此实现族外婚、氏族间的盟誓审判。在祭天时宰杀白马,缘于北方游牧民族对白色的崇尚和对天的尊崇。
满族萨满祭祀中的蒙古神形象
除“敬天”的传统外,满洲文化中的萨满信仰也是凝聚氏族和部落情感的纽带,在此信仰体系中,每个部落中有德行的氏族先祖会成为祖先神而被祭拜。随着满蒙联姻的不断持续,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之女嫁入满洲,她们也都会携带娘家氏族祖神神偶到夫家供奉,这是母系氏族祖神与女性联系牢固的古俗遗风在父系氏族社会的延续。因此,满洲萨满祭祀中就出现了喀屯诺延(蒙古族王妃的先祖)这样的“蒙古神”。
入关后,宫廷萨满祭祀成为清王朝的国家宗教形态之一。在具备完整的祭祀体制的同时,又形成了传世经典《钦定满洲萨满祭神祭天典礼》来规范祭祀仪式的主体、程序、仪规以及祭祀用具。所祭诸神中,除佛、菩萨、关圣、夕祭神等神灵外,蒙古神更是赫然在列。作为祭拜对象的“蒙古神”——喀屯诺延,能够得到清朝帝王及宗亲的承认,并被写入典籍当中,成为定制,这表明蒙古元素通过民族交往、交流已经深深植入清王朝文化中。
皇太极的文化形象是多元、立体的,他针对王朝疆域内信持各种文化的族群,举行有所侧重的“理解”“表演”仪式,完成形象塑造。因此,他不仅仅是八旗共主,还是蒙古诸部的“博格达汗”;面对汉人,他是维系道统的“圣贤明君”。皇太极参与仪式建构与表演、塑造多元的王权形象等举措对清王朝的后世统治者是有借鉴意义的,随后的清朝诸帝只需亲善蒙古、遵循“蒙古情感”,便可得到蒙古的承认,承袭“博格达汗”的称号。推而广之,当随后的清朝诸帝广泛参与到这些基于政治考虑的各种“仪式表演”中,便能够解决随着王朝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出现的新的民族、宗教、文化认同问题,实现对域内信持各种文化的族群行之有效的统御,有助于清“大一统”王朝的建构。
(本文系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一般项目“乾隆皇帝菩萨王形象塑造研究”(NWNU-SKQN2019-32)阶段性成果)
上一篇:试论商纣王身世之谜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