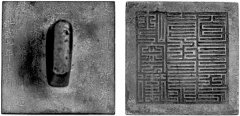民族融合与历史书写:《元史》蒙古列女形象“汉化”问题刍论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元代蒙古妇女守节乃是受到汉文化之深刻影响。通过考察《元史》所载蒙古节妇具体事例,并结合同时代蒙古、波斯文献以及外国人游记收录的有关蒙古妇女守节的内容,《元史》所载蒙古妇女守节与其汉文化水平并无直接关系。她们的这些行为是明朝政府出于巩固政权、推行风教等目的,以及受到理学发展之影响,而被加工、重塑后列入《元史》当中以加强文化认同。《元史》有关蒙古列女形象的书写,恰好反映出元明之际多民族交融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蒙古节妇 《元史·列女传》 历史书写 元代 民族融合
作者简介: 肖超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合作导师为刘正寅研究员
《元史·列女传》里记载了一则值得注意的材料:“脱脱尼,雍吉剌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剌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壮,无妇,欲以本俗制收继之,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复百计求遂,脱脱尼恚且骂曰:‘汝禽兽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二子惭惧谢罪,乃析业而居。三十年以贞操闻。”①一般认为,元代蒙古社会盛行收继婚,②那么如此情况下,脱脱尼以死拒绝再嫁,并将这种收继习俗斥为“禽兽行”,岂不是有悖蒙古社会传统的“逆举”吗?为何后世史家却视之为“列女”,将她塑成道德的榜样?果真如部分学者所言,以脱脱尼为代表的蒙古妇女自发的守节行为皆是受到汉化、理学的影响,③或者另有其他原因?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试图对元代蒙古妇女贞烈事迹书写背后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元代蒙古妇女守节的行实,主要集中在《元史》里。除前引脱脱尼事外,《列女传》尚有只鲁花真(蒙古氏)、贵哥(蒙古氏)、也先忽都(蒙古钦察氏)、卜颜的斤(蒙古氏)诸人或誓不贰婚,或以身死节的记载。其中,也先忽都、卜颜的斤二人遭遇相近,皆因将面临战乱被俘,而选择殉节。史载也先忽都为大宁路达鲁花赤铁木儿不花妻,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攻破大宁,时铁木儿不花已坐事免官,而也先忽都被擒后仍称“我达鲁花赤妻也”,拒绝为敌效命遭到杀害。④然而,实际上大宁路为红巾军所破当在至正二十年(1360),《元史·顺帝本纪》载:至正二十年春正月“癸卯,大宁路陷”,⑤此前大宁路仍属元廷掌管,⑥所以该则材料时间记载有误,致使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卜颜的斤乃宗王黑闾之女,黑闾其人暂不可考,明军攻破大都时,卜颜的斤谓其夫观音奴曰:“我乃国族,且年少,必不容于人,岂惜一死以辱家国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先忽都死后,其子与夫出城就执于敌,子乃请以身代父死,“贼爱完者姿秀,遂挈以从。久之,乃获归脱,访母尸并玉莲葬焉”,⑦玉莲是铁木儿不花妾,其与也先忽都皆见杀,也先忽都子完者后来合葬其母与父妾,可推知当时铁木儿不花并没有死。至于卜颜的斤,《列女传》记其向观音奴交待完后“遂自缢而死”,说明她也是亡于夫前。据此观之,也先忽都、卜颜的斤选择殉节,或许更多地出自她们的(族群)自尊心,而不一定与其汉化程度高低有关。
贵哥拒嫁的事例比较特殊,《元史·列女传》载:“贵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罗五十三妻也。天历初,五十三得罪,贬海南,籍其家,诏以贵哥赐近侍卯罕。卯罕亲率车骑至其家迎之。贵哥度不能免,令婢仆以饮食延卯罕于厅事,如厩自经死。”⑧可见贵哥因其夫罗五十三遭流贬,而受到牵连。一般认为,元朝的流刑遵循“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的原则,而由于元代流刑犯是终身不赦,所以法律通融规定:“妻子从流,听。”⑨但是此处贵哥却被元文宗下诏赐给近侍卯罕,说明其人身自由已遭限制。类似的有至元二十八年(1291)行台监察御史周祚因得罪桑哥,被流于憨答孙,妻子家资入官。⑩结合周祚遭流、妻子入官的经历,或可认为贵哥时已没入官籍,属于“官家财物”,因此才会被赐予他人。所不同的是,周祚平反后朝廷“复其妻子”,而贵哥眼见拒婚无望,于是选择了自杀。虽然在天历二年(1329),曾有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对罪臣之妇的处理方式不满,向朝廷建议:“人伦之中,夫妇为重。比见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断付他人,似与国朝旌表贞节之旨不侔、夫亡终制之令相反。况以失节之妇配有功之人,又与前贤所谓‘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之意不同。今后凡负国之臣,籍没奴婢财产,不必罪其妻子。当典刑者,则孥戮之,不必断付他人,庶使妇人均得守节。请著为令”,(11)但统治者似乎并未采纳这一建议。而且元文宗曾表示“流窜海岛,朕所不忍”,竟对曾以贪赃得罪、矫诏独行、私测皇帝在位时曰长短的前丞相别不花网开一面,御史原本建议“宜窜诸海岛,以杜奸萌”,但最终只是“并妻子置之集庆”。(12)相比之下,罗五十三却没能得到皇帝的宽恕,不仅身遭流贬,妻子也受到连累。贵哥身为罪臣之妇,抗旨不遵而死,从元廷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为其旌表节义。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