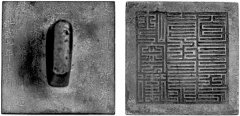刘增光:孔子的心学与史学——钱穆《论语》学探微
内容摘要:钱穆一生对《论语》用力颇多,他对《论语》的理解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不言心性本体,而以人与人相与之人道、人人情感相通之人心言说儒家之仁学;二是以对学脉、学统的重新梳理,反驳宋代理学的道统论及由此而来的历史观,从而展露出对儒学发展整体和中国人文历史全貌的关怀;三是吸纳公羊学之相关论述,重视孔子所作《春秋》,一方面强调孔子之“信而好古”,一方面强调孔子之新创法度。究其原因,这三个层面正代表了他对近代中国儒学和孔子命运的思考,显露出他个人的学术抱负,欲在经学路径、西学路径、哲学路径之外另辟一条理解孔子和兴复中国文化之路。此路径之缺陷诚然有之,但其贡献亦不可抹杀。
关键词:孔子;心学;史学;钱穆;论语
作者简介: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课题: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单列课题“近代中国阳明学的学术史研究”。
钱穆研究《论语》贯彻一生,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即是《论语文解》,其时在1918年。此后于1924年撰成《论语要略》,1935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其中考订孔子生平。1952年在《论语要略》基础上作成《四书释义》,①1963年出版《论语新解》,1974年撰作后来被译介至日本的《孔子传》。此皆述其有关《论语》与孔子之专著,若综观其相关之单篇论文,则更为洋洋大观。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两篇专文即是:约作于1970年左右的《孔子之史学与心学》与《孔子之心学》,其中提纲挈领地阐述了自己对孔学的理解。但要探究钱穆的《论语》学,仍应以最为详备的《论语新解》为中心,由此旁涉他书。
归纳起来,钱穆对《论语》的理解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不言心性本体,而以人与人相与之人道、人人情感相通之人心言说儒家之仁学;二是以对学脉、学统的重新梳理,反驳宋代理学的道统论及由此而来的历史观,从而展露出对儒学发展整体和中国人文历史全貌的关怀;三是吸纳公羊学之相关论述,重视孔子所作《春秋》,一方面强调孔子之“信而好古”,一方面强调孔子之新创法度。据此三点,钱穆以明确的思想史、儒学史视野,绾合经史,兼采汉宋,包罗今古二学,试图重新回归孔子之本真。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大语境中有着重要意义,其《论语》学卓然自成一家。但应当指出的是,钱穆从史的视野观照《论语》,忽视了如何在一个平铺的历史序列中建立价值标准的问题,相应地他也未予孔子之道德精神和超越性境界以应有的关注。因此他虽然认为孔学是史学心学二维相须,但终究偏于史学。这一点,在他与现代新儒家徐复观的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发生在新儒家内部的这一争论恰似七百多年前的朱陆之辨,至今犹有回响,思考儒学之未来,不能不予以深思。
一、人道必本于人心
“人道本于人心”为钱穆《论语新解》的纲领性命题,脱离此命题便不能得钱氏理解孔子之真精神。不过,需要分析的是,钱穆所说“人道”“人心”与前人相异。钱穆以为人道就是人群相处之道,侧重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关系。人道必本于人心,因为人群社会之成立要以人之道德人格的养成为基础。同样,这也意味着人之成德必在人与人之关系中达至,故其言人心亦非个体之心,而是强调人人皆具而相通的人心。一言以蔽之,人道与人心二维一体。
我们知道《论语·学而》首章并未言“心”,正如钱穆所看到的,《论语》全书“讲及‘心’字亦极少”。②但钱穆解释此章却说:“学能时习……心中欣喜也。”“悦在心,乐则见于外。”③并阐发其意,认为孔子之学皆由现实生活中的“真修实践”而来,而此真修实践则必兼“心地修养与人格完成之两义。”④人格完成之道就是人道,而必本于心地修养。这意味着钱穆在《论语》开篇的解释中就灌注进了“人道本于人心”的命题。于是,他在对紧接着第二章“本立而道生”的解释中直接将此命题揭领出来:“孔子之学所重最在道。所谓道,即人道,其本则在心。人道必本于人心,如有孝弟之心,始可有孝弟之遭。有仁心,始可有仁道。”⑤可以看到,孝弟之道、仁道皆是人道。孝弟之心、仁心皆是人心。正如《论语·公冶长》中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道即人道”之说正表明钱穆对天道的悬搁,故他也并不像宋明理学家尤其是朱熹那样必以本体和发用、性体情用来理解仁与孝之关系。对此,他屡有述及,如: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