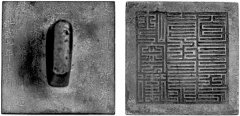亲情与门风:从嫂叔关系看魏晋时期的女性、家族与文化认同
内容摘要:《丧服》规定嫂叔无服,缘于名分的限制与实际生活中的避嫌。但是这一规定却在魏晋时期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论,对立双方或维护传统,或因应现实,观点迥异。整体而言,主张嫂叔之间无服的观点更被社会认可,也更为通行。这与魏晋时期重视门阀家风、讲究闺门整肃的现实需求有关,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女性地位的提高,风气所及,连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族也深受影响,并成为是否取得汉人士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前提。尽管有北朝恒代遗风的影响,以及玄学的兴起、重情观念的流行,“情”“礼”冲突频仍,率性、放达成为最时尚的生活姿态,以致以往所有的思考都需要重新思考。但是需要关注的是,当事关世族门风、胡汉关系、皇权正统等大事时,传统之“礼”仍会占据上风。这种既对抗又妥协的胶着状态,嫂叔关系正是绝好反映。
关键词:魏晋时期;《丧服》女性;嫂叔;家族
作者简介:张焕君,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礼学史。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项目编号:14ZDB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儒家经典文本,《丧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记载的只是丧礼,但是因为生老病死,不分尊卑,人人都须面对,而且这种面对不仅仅是仪式、器物等外在形式的采择,更涉及通过服丧而明确的五服关系以及个人在服丧时如何调节心中情感、如何区别死生等诸多问题,就使《丧服》的内容远远超出单纯的丧礼的范围。所谓五服,本来是丧服的五种等级,用来表示生者与死者的亲疏远近,但实际上它更重要的功能却是在于确定生者与生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构成家庭最基本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到试图区别同姓、异姓以及亲疏的九族、宗族关系,乃至国家层面上模仿父子的君臣关系,莫不在《丧服》的关注之内。不仅如此,它又通过外在的服丧方式与内心情感变化之间的适应,提倡亲亲、尊尊,追求“情”与“礼”的和谐,建构一个立足于血缘关系但却有层次有差别的完整体系。
但体系的完美并不等于现实的认可。社会背景的变化往往导致对经典的重新解释。既有解释,则必作损益,而损益的标准往往依违于经典与现实之间。没有完全的割裂,也没有完全的创新。所谓除旧布新,正在于传统与现实的妥协与中庸。魏晋之世,战乱频仍,思想却极为多元而丰富。乱世本易生伤怀流离之感,玄学、佛教的流行,更使人间真情超越外在的礼法约束[1](PP324-325),成为重新评价传统经典的基点。这样的观念转型,在时人对丧服制度的持续讨论中比比皆是。嫂叔关系,便是其中一例。嫂叔本属平辈关系,但是因为名分所限,加上大家庭同居生活中在男女关系上的有意防范,竟使这种在实际生活中极为亲密的关系,在丧服上反而毫无体现。不合常理之处,引得后世学者纷纷立说,或辩护,或驳斥,态度激烈。所以如此引人关注,正在于它既是一个礼制内部问题,又是门阀社会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更与魏晋时期女性地位的改变乃至文化认同上的华夷之辨密切相关。经典与现实胶着,礼义与人情交错,没有截然的是非对错,历史的曲折起伏却尽在其中。
一、嫂叔无服:名分对情感的遮蔽
《丧服》中对于血缘关系较远、服制较轻的亲属,专门设立加重的服制。加重的原则主要依据名分,即“以名加”,如为从母(姨母)、庶母、乳母,乃至从母昆弟(姨兄弟),都是因为有“母”之名,故服制加重一等。嫂叔之间虽然关系亲近,但因为无法纳入母、妇之“名”这一系统,以至双方互不服丧。但礼缘情而制,无论是“名”还是“母名”,其下隐藏的都是情感和恩情,一旦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情感的考量便难以避免。嫂叔关系正是如此。《礼记·大传》云:
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2]?
嫂叔之所以无服,正是因为“名”的缘故。郑玄注云:
言母、妇无昭穆于此,统于夫耳。母焉则尊之,妇焉则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己伦,以厚别也[2]。
母、妇之名,一尊一卑,通过尊卑的名分,提示嫂与弟妇都不像可以与自己敌体判合的妻子那样,以此来加强身份上的区别。郑注又云: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