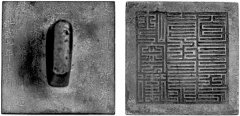【文萃】帝学视野中的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
经筵名称及其制度源流认识检讨
经筵是宋代为帝王专设的御前经史讲席。从南宋开始,“经筵”一词被泛用,时人将汉唐以来讲经侍读活动皆视为经筵。自最早全面论述宋朝经筵的开山之作朱瑞熙的《宋朝经筵制度》问世之后,学界对经筵概念及其制度源流进一步地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做了明确的区分与界定(简称两分法),代表性观点认为,“广义的经筵指汉代以降,皇帝亲自参加的学术活动。狭义经筵专指北宋确立的有专门法规保障,在专门机构组织操作下,由任专门官职的儒生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强调“专门机构、专门官职、专门法规、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固定科目”六个条件是经筵制度确立的标准,六个条件首次齐备的北宋仁宗朝是经筵制度正式确立的时间。
两分法对宋代经筵制度性特点的强调完全正确,但对经筵概念及其源流的厘清不够彻底。两分法可以视为对南宋人泛用“经筵”的纠正,但这种纠正既未探究南宋人泛用的原因,也未对泛用的合理性与适用度作出分析。两分法将汉唐讲经侍读活动定义为“广义经筵”,具体而言,有三点不妥。
第一,从词源来看,“经筵”之名首次出现在宋代,正反映了讲经侍读活动在宋代以制度形态成熟定型、从而迥别于汉唐讲经侍读的历史进程。两分法将汉唐较为松散的讲经侍读活动统统冠以宋代才出现的“经筵”之名,时间上有以后概前之嫌。而且广义概念对“经筵”专名特有的制度化含义做了消解,狭义概念对“经筵”专名本来就具有的制度化含义做了重复强调,实际上都是过于缠绕的概念“语言浪费”。
第二,从划分标准来看,两分法标举的唯一标准“制度化”,在实际研究中并未贯彻,反而存在概念界定之外的多重隐性标准。以对视学礼的处理为例,按照两分法,汉唐视学礼属于广义经筵的范畴,宋代视学礼从研究标准上却不能纳入宋代经筵的范畴,在两分法中无处存身。换言之,概念界定标准由客观“制度”因素悄然转变为主观“意图”因素,这种事实上的双重标准存在有违学理逻辑之嫌。
第三,从制度背后的内容实质来看,两分法没有充分认识到汉唐讲经侍读活动与宋代经筵的区别不仅在于客观上的制度化,还在于主观上的权力授受关系不同,这一更具内容实质意义的变化因素体现了宋代政治、学术中士大夫地位和作用的加强与提升,是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的根本区别。
南宋人泛称“经筵”的合理性及其适用边界
南宋时人将汉、唐、宋讲经侍读活动统称为“经筵”,不仅因为宋代政治文化对汉唐源流有攀附追认的惯例,意在声明其制度建立的合法性,更在于宋代经筵与汉唐讲经侍读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个别特殊历史情境的契合与某些制度性因素的承袭。但这些契合、承袭因素要经过严格的概念界定,要在全部历史事实中衡量其份额及作用,以明确其适用边界。
1.汉代特殊历史情境下讲经侍读的两种变化
第一种,汉代太子即位之后,以皇帝身份聆听太子时期的师傅讲授经典。此时“帝王”“经师”两种新身份中还延续了旧日太子接受东宫师保教育的程仪与尊重。西汉成帝时期“金华殿讲经”在行为程式化、尊重讲官两个层面上,曾被宋人视为经筵的前身。第二种,为幼帝讲经。如果皇帝以年幼即位,原本应该在太子储位阶段完成的“为太子讲经”,在名分上则变为“为皇帝讲经”。这以东汉末灵帝“华光殿讲经”最为典型。“金华殿讲经”“华光殿讲经”与汉代著名的“石渠讲经”“白虎观讲经”中皇帝聆听经师论辩后裁决经学本旨的情况截然不同,更多是帝王以接受经师传授内容观点的方式学习经典。换言之,是皇帝还是经师持有理解经典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金华殿讲经”与“华光殿讲经”确实更接近于宋代的经筵。然而,“金华殿讲经”“华光殿讲经”的出现是基于特殊历史情境,属于汉代讲经侍读的变形而非常态。南宋人论及本朝经筵时追述“金华殿讲经”“华光殿讲经”存在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不能将特殊个案作为汉代讲经侍读活动性质的判断依据。
2.唐代侍读活动中的某些制度性因素对宋代经筵的影响
“金华殿讲经”被南宋人认为是经筵制度化(“经筵有常”)的开始,但是尽管此时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人员、时间、地点乃至形成讲义,然而它与宋代经筵制度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在职官设置上还未能制度化。唐代讲经侍读职官的设置对宋代经筵有所影响,玄宗开元三年(715年),设置集贤院侍读,稍后,设置集贤院侍讲学士。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设置翰林侍讲学士。
上一篇:明清地方档案的整理与出版亟待规范
下一篇:中国古代刑事法制的历史特点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