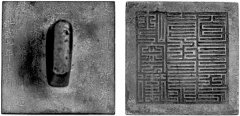从秦汉北边水草生态看民族文化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分析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规律性现象,指出草原和海洋对文化交流的作用。他写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腊航海家们曾经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言,虽然自从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隔离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在近年来英语也就变成世界流行的语言了。”汤因比指出,“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就便利交通的作用而言,草原和海洋有同样的意义。草原为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草原这种“大片无水的海洋”成了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草原象‘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235页)中国上古文献不使用“草原”这一地理语汇,但注重“善水草”(《史记·李将军列传》)、“水草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水草之利”(《汉书·赵充国传》)对游牧射猎经济的意义。“逐水草迁徙”“逐水草移徙”(《史记·匈奴列传》)、“逐水草往来”(《汉书·西域传上》)的历代民族的发育、强盛及其活跃表现,促进了欧亚大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进步。
从“弱水”“流沙”看草原
上古时期,中原人似乎注意到了草原”和“海洋”两种地理样态对于文明融汇的相似意义。对于后世所谓的草原”地貌,他们习惯使用“大漠”“流沙”“瀚海”等似乎与“海洋”有关的称谓。华夏文化的边缘“西至于流沙”(《史记·五帝本纪》),中原王朝的版图西被于流沙”(《史记·夏本纪》),甚至秦始皇宣布其统一帝国的疆域时,自称“西涉流沙”(《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外,汉武帝歌诗言“天马”之来:“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记·乐书》)
长期“转牧行猎于塞下”的“胡人”(《汉书·晁错传》),以其文化风格为中原人所瞩目。对于他们的进取意识和尚力之风,汉人称为“狼心”(《后汉书·南匈奴传》)、“其性悍塞”(《后汉书·乌桓传》)。汉人还注意到他们与中原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其“贵壮健,贱老弱”“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然而关于双方“礼义”方面的差别,汉使与汉人降匈奴者中行说的辩论,《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述中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态度。
出土于湖北鄂城的一面汉镜,铭文可见“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体现中原人对西北方向的特殊关注。对于西域绝远之国的探索,司马相如赋作言,“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涉流沙”(《汉书·司马相如传下》)。相关知识应当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向东传布,博望侯“凿空”之后则全面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认知。
相互往来促进民族融合
秦汉人习称北部边地为“北边”,时有“北边郡”和“内郡”的对应关系。当时虽然也有“南边”和“西边”的说法,但是“北边”为朝廷上下密切注目,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关心。这是因为这个方向存在着匈奴这一强势政治实体。由于交通能力与机动性方面的优势,其军事力量对汉地农耕社会造成严重威胁。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写道:“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指出, 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他们特别重视民族关系在这种“交往”中的动态:“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这种形式“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秦汉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具有军事强势的“征服者民族”匈奴,就曾经“广泛地利用着”这种“交往形式”取得战利。即使在战争状态下,据说“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史记·匈奴列传》),依然“关市不绝”。而战争形势的需要,也使得汉王朝兴起马政,发展屯田,繁荣了“北边”经济。由汉王朝的行政中枢,可以看到“胡巫”影响中原人信仰世界的表演。“胡骑”甚至成建制地在汉军中服务。而“胡贾”“入塞”之后在经济生活中的活跃表现,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激活作用。汉家百姓亡入胡地,也将中原掘井筑城等技术带到草原,影响了那里的经济生活。
上一篇:元净州路故城汇聚多元文化
下一篇:蒙古考古遗存特征鲜明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