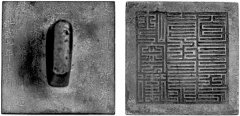石峁古城性质再认识
2010年以来,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得到系统开展,陕北一隅开始成为探索中华文明发生与早期发展的焦点。石峁古城被发现之后,一些学者注意将其与古史传说人物及部族相联系。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的对证不失为一个探索方向,但在实际研究中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考古如何与传说对证
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之初,便与探寻“夏墟”“殷墟”紧密联系,并被赋予“重建古史”的特殊使命。因此,在每一项重大考古发现问世之后,学者习惯在古史传说体系中对号入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具体操作上,至少需从以下方面考虑。
其一,“时”。时代的对应是首要前提,若忽视年代框架的限定,容易陷入“关公战秦琼”的窘境。但作为基本前提的时代因素,同样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古史传说的相关记载语焉不详甚至矛盾丛生,如夏代纪年可相差百余年,再如上古人物或部族的时代难以准确落实,甚至其历史真实性都是很大问题。另一方面,出于考古学自身特点,我们能够充分认识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但在认识绝对年代方面仍有较大局限性。近年来,“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调整带来的一系列争论,便是典型例子。
其二,“地”。地域的对应至为重要,但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不少困难。先秦古籍中的地名多缺乏准确定位,汉晋时人虽多有解释,但仍存较大的时代鸿沟。伴随传说的流布、后裔的拓殖、地名的移植,古地名往往歧说迭出,莫衷一是。不少论者往往根据某部族后裔分布于某区域,便认为该部族居于该区域。如若未能动态考察族群的流散,则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此外,考古学文化与部族文化之间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在复杂社会阶段尤其如此,二者的地域范围未必是重合的关系;诸如良渚、陶寺、石峁等大型城邑往往与统治阶层相关,可作为空间视角的重要切入口。
其三,“人”。徐旭生、蒙文通等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大抵分为华夏、苗蛮、东夷诸集团。其中一些古史人物,如蚩尤,或归诸东夷,或归诸苗蛮,仍有较大争议。此外,统治阶层与百姓的族属未必等同,且人群存在流动与交流,有必要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加以考察。就考古发掘的先民遗骸而言,传统体质人类学及分子人类学为探究先民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由于目前相关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不足,学科间的合作也不够充分,仍难以为考古与传说的对证提供直接证据。
其四,“物”。考古学难以像文献材料那样提供具体史实,难以还原先民活动的诸多细节,在重构古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构建,主要通过陶器,但很多时候陶器只能反映“小传统”。随着社会复杂化的推进,“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野逐步加深,承载“大传统”或精英文化的因素(如玉礼器、神灵崇拜)尤其值得关注。
其五,“文”,即直接的、共时的文字材料。晚商之前虽有零星文字或刻画符号发现,但尚难以构成完整证据链中的核心一环,这也是一些学者不承认夏朝及五帝时代的重要原因。无论夏朝抑或五帝时代,相关考古学文化虽不同程度地满足“时”“地”“人”“物”诸条件,但均缺乏自证性材料,故只是合理程度不同的假说。目前,陶寺遗址作为尧都、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都,得到国内学者较多认同,但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材料,且遗址本身尚存疑点,同样只能视为假说。
石峁古城性质诸假说
目前学者关于石峁古城族属的推测虽仍属于假说层面,但其中一些说法不无启发性。沈长云所倡“黄帝居邑说”最为人所知。王红旗、李宗俊等有类似看法。以下试作辨析。
首先看“时”。笔者曾质疑“黄帝居邑说”,一个重要顾虑便是黄帝时代与石峁古城年代不合。石峁古城的时代相当于夏朝建立前后,与陶寺古城约略同时,在考古学上属于“龙山时代”,与通常认识中的黄帝时代不尽相符,在“时”这一层面存在矛盾。黄帝的年代未必在五千年前,但其在尧、舜、禹时代之前,应为先秦秦汉时人的普遍认识。
其次看“地”。石峁古城所在的陕北地区有较多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但类似传说也见于其他区域,如河南也是黄帝传说和遗迹的分布区。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在司马迁的时代,黄帝传说已经广布大江南北。黄帝与陕北的关系值得重视,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区域与黄帝相关的可能性。
上一篇:“小邾”何以立国
下一篇:2019年宋史研究述评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