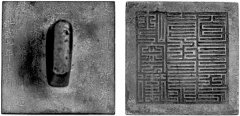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
■本期主题:历史与考古双重视域下的夏王朝与夏文化 ■本期主持: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主持人语
夏文化问题某种程度上像是中国考古学孜孜以求的“皇冠上的明珠”,其争论的核心实际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认识论的哲学问题,关涉的是考古学者的立场与方法。五四以来,古史辨派学者有力地挑战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上古史学的“元叙事”,而傅斯年则转而采取“史学即史料学”的守势,这两种史学思想都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无论是前者批判上古文献为传统史家的层累造成或神话的伦理构建,还是后者试图效法自然科学范式以重建科学的上古史,其实都遮蔽了历史的“生成性”,抽离了历史中的人。事实上,材料的真伪、证据的充足与否,仍属于方法论的表层,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的视域融合和语境释读,与追问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关联起来,才能避免考古学沦落为冰冷的技术研究,才能避免失却中国考古学从古史重建到文明阐释的人文关怀底色。
夏文化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命题,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追求,很多问题趋于清晰,但在一些关键认识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归纳来讲,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于夏代信史地位的基本态度,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基本方法以及论证夏文化的基本证据。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夏代究竟是信史还是传说,这是夏文化探索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上个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对大禹的属性产生了怀疑,顾先生主张禹本是天神,后转化为人王,再与夏代发生联系。虽然顾先生本人从未对夏代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但“疑古”思潮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不少人主张中国最早的信史只能到晚商,夏代即便不是出于后人的建构,但在发现当时的文字证据之前,其信史地位仍然存疑。
夏代的信史地位涉及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以及对历史和历史叙述的认知。从传世文献来讲,除了《史记·夏本纪》的系统叙述之外,在《尚书》《左传》《国语》和《诗经》等先秦文献中都有大量关于大禹或夏代的记载。在出土文献方面,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王国维就已举出秦公簋和叔夷钟的铭文来证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著名青铜器豳公盨,铭文开首即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证明最晚在西周中期《尚书·禹贡》里的相关内容已经广为流传。
虽然这些材料均属两周时期,距离夏代尚远,但这恰恰是历史叙述的正常形态。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其中必然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既可以是真实的,也难免有想象的成分。神话和传说,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包含有较多历史想象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大禹这类历史英雄人物,更容易被“想象”,被神话,这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如果因为这些想象和神话成分就否定大禹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无疑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史料甄别是古往今来所有历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司马迁也曾困惑于百家言黄帝的“不雅驯之言”,但太史公并没有因噎废食,断然否定黄帝,而是善于裁断,“择其言尤雅者”而著成了《五帝本纪》。对于治中国上古史的学者而言,最需要的是一双能够鉴别“历史想象”和“历史记忆”的慧眼,努力区分神话、传说和史实,寻找神话和传说中的“真实素地”。如果以当时的文字证据作为信史的唯一标准,看似严谨科学,实际上是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叙述,贬低了历史文献的应有价值,也失去了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应有尊重。
退一步讲,即便以文字证据而言,也不能就此认定夏代非信史。虽然目前成系统的最早文字材料见于安阳殷墟,但在郑州商城以及郑州小双桥等商代前期遗址中,也发现了零星的文字材料。更重要的是,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与甲骨文属于同一文字系统的朱书陶文,时代则属于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时代。以此类推,夏代并非没有文字,只是目前在考古学上尚未发现而已,“以不知为不有”,是考古研究的大忌。
二
1959年徐旭生先生对“夏墟”的调查,是真正意义上的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开始,六十年来,几代考古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从方法层面而言,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大体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夏都法”,一类是“夏墟法”。
上一篇:辽朝宫卫组织演变历程
下一篇:从考古大发现到古史研究黄金时代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