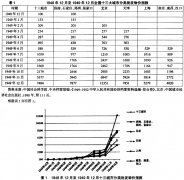“记忆”研究的可能性
一、从“记忆之场”到“历史之场”
“记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开始于20世纪的70—80年代。源自欧洲的“记忆研究热”西进美洲,东渡日本,波及了东西方的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记忆研究的代表作法国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重新思考法国——记忆之场》等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至今依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以“记忆之场”为代表的历史研究的主要学术指向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成立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的“传统”、“民族记忆”是如何通过国旗、国歌、纪念碑、纪念集会等形式被创造、被表象的。用诺拉自己的话说,就是“想用不同于纪年式的方法来研究法国的国民感情,也就是通过对凝聚了法兰西集体记忆的各类场所的分析,来勾勒出一幅法兰西象征物的俯视图”。诺拉用“历史在加速”来表现近代以来的变化。他提出“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的终结”的结果导致了“记忆之场”存在的必要。所谓“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的终结”,是指在不断反复的时间中,与过去(记忆)共生的集团中(诸如农民集团),那些被认为是典型的被身体化的过去(历史)消失了。这不仅限于农村,家庭、学校、国家等确保价值的保持、传达的“与记忆一体化的共同体”都趋向消亡,由此造成“从遥远过去开始的事象终于走向消亡”的历史断裂感。诺拉说,如果我们保持着记忆,那就不需要记忆之场;因为,没有导致记忆消亡的历史的存在,也就没有记忆之场的存在。这时,所有的动作,包括最细微的日常活动,都像古昔传承下来的信仰那样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动作、行为以及意义都是与肉体融为一体的。但是,一旦痕迹、距离和媒体登场,我们就不再处于记忆之中,而是处在历史当中了。关于记忆和历史的关系,诺拉认为,记忆是当下的,是永远以现在时呈现的,是感性的、特殊的、象征的,而历史是基于知性,建立在分析与批判基础之上的。日本学者小关隆则更为明快简捷地说,在社会中共存的诸多记忆中,经过某种政治的、学术的、文化的认可的公共记忆就成了“正史”(official history)。
在《重新思考法国——记忆之场》出版后的三十多年中,又有无数以记忆为对象的论文和著作问世,其中不乏对诺拉研究范式的模仿复制,即用相同或类似的问题意识和手法把研究的对象延伸到其他各国。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新的成果出现。例如,2010年,一批日本西洋史学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之场——史迹、纪念碑、记忆》的著作。这个书名很明显是针对“记忆之场”而起的。这部书探讨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东欧和北欧等地的纪念碑、墓地、历史遗迹的形成背景和经过,分析了这些被作为表象物创造出来,然后被传承、抹消或忘却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复杂的社会力学关系。关于这部著作的主旨,主编之一若尾佑司说,诺拉的“记忆之场”的研究重心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记忆是如何被唤起、建构起来服务于塑造同质的国民的。但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那些记忆的象征物比如战士墓地、英雄纪念碑等已经不再带有其诞生之初的激起民众的狂热的魔力。它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遗产化”。联想起在世界范围内的“世界遗产”申请热潮,若尾认为,这些渗透在全世界的遗产热,从原有的国民纪念碑等扩展到了地域性的历史、自然遗产,甚至延伸到了过去被国家公共记忆排除的少数人群以及被封存的国家暴力的牺牲品的记忆。这些原本被抹消、被忘却的记忆,如今以文化遗产的名目成为打开通往过去的“历史之场”。①透过这个历史之场,记忆不断被生产、消费。其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层面,而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从“记忆之场”到“历史之场”,标志着记忆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也为人们研究当下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观察当今中国记忆的研究,在探讨近代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记忆”作为国族认同建构过程的分析,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成果。例如,岳飞形象的再造,孙中山纪念物的诞生等。②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中,大量的社会记忆被整合、封存、抹消、忘却。例如,近年来在各种媒体中悄然出现的有关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反右、“文革”、唐山地震等历史事件的“非正史”的或可称为民间叙事的爆发性的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认识,有些甚至会颠覆现有的历史研究所做的结论。本来,多元的、不同层面、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记忆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而通过对这些被忘却的记忆的挖掘和整理,展现出一个社会的多层性和记忆的多样性,应该是当下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记忆的主观性与身体性
记忆研究虽然蕴涵着丰富的可能性,但作为方法,它一直处在探索和争论之中。在历史学领域,过去往往将记忆作为历史的对置概念,认为历史是客观的、科学的、可靠的、不变的,而记忆则是主观的、感性的、多变的。因此,在采用诸如口述史的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鲜活的记忆资料往往要被拷问是否“客观”、“真实”。就连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以口头传承为主要对象的民俗学,也曾经有过如何确认口述的民俗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的讨论。这种议论的共同点就是,将口述资料当作另一种文献看待。在更多的时候,口述的声音资料被记录成为文字,成为文献资料的补充。但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兴起打破了这样的格局,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承认主观性和身体性本身的价值。例如,英国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赞同如下观点:“恰恰是被某些人视为口头资料来源的一个弱点的主观性,也可以使得这些来源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因为主观性与更加可见的事实一样,也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被访者所相信的东西确实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他或者她相信它这一事实),就像‘真正’发生的东西一样。”③
对于口述资料的不真实的可能性,波利特认为,“‘不真实’的陈述仍然是心理上‘真实的’,并且这些以前的‘谬误’有时比实际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口头资料的来源的可信性是一种不同的可信性……口头见证的重要性经常并不基于它对事实的依附,而是会基于它与事实的分歧。在这里,想象、象征、欲望破门而入”④。汤普逊进一步指出,“历史学不仅是有关事件或者结构,或者行为模式的,而是有关这些东西如何被经历和在想象中如何被记住的。而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想象发生的东西,也是他们相信可能已经发生的东西——他们对于一个可供选择的过去,也是对于一个可供选择的现在的想像——可能与实际发生的东西同样至关重要”⑤。
波利特提到的“想象、象征、欲望”,可以说是记忆形成的本质性的要素。正是这些主观要素的存在,构筑了一个与“客观事实”不同的“主观事实”,然而事实上,影响人们生活的往往是这些“主观事实”。日本社会学家家樱井厚援引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J. S. Bruner)的人生三分类,即“作为生活的人生”(life as lived)、“作为经验的人生”(life as experienced)、“作为叙事的人生”(life as told)来讨论体验、经验、叙事的关系。所谓作为生活的人生,就是生活体验本身,通过行动表现出来,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客观存在的生活事实。而作为经验的人生,则是伴随叙述者的印象、感觉、感情、欲望、思想、意义而成立的,是记忆的本源。它在被唤起的时候,会根据当下的情境重新构筑。至于作为叙事的人生,是通过日记、自传、备忘录等手段文字化的人生,也包括口述采访的记录稿等。⑥
《百年孤独》的作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所谓人生,并非是发生的一切本身,而是对发生的一切的回忆,以及唤起这些回忆的过程。”换言之,作为生活的体验,是一次性的,而它对人生的影响是体现在作为经验的人生中的;作为经验的人生,就是记忆的本质,它通过文字的书写和非文字的口述表象化,而这个过程是“伴随叙述者的印象、感觉、感情、欲望、思想、意义而成立的”。
记忆的主观性和身体性,在战争记忆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笔者调查的日本老兵的战争记忆资料里,虽然不乏对当时在受害国烧杀掠抢的反省,但是更多的是对战死的战友的追忆,自身在战场受伤、恐怖、饥饿、劳累,以及被俘后在苏联服劳役的痛苦经历。他们的家属的记忆则是在后方节衣缩食、蒙受美军轰炸,自己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在战场战死给全家带来的巨大伤痛等。虽然这些身体记忆使他们对战争有本能的厌恶,而他们无法接受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友是“犬死”的结论。作为对自己和死去的战友的人生价值的肯定,他们之中不少人虽然承认侵略战争的事实,但也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因为他们把靖国神社当作能体现死者人生价值的场所,是他们消解丧失亲人的痛苦记忆的装置。
因此,要全面了解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就必须把握记忆的主观性和身体性特征。从客观真实的层面来说,日本是加害国,但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却大多是受害记忆。这个受害记忆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上述战时的身体体验,另一方面也来自掩蔽战争加害者的主观愿望。记忆的主观性和身体性导致了对事实的误认,但是,这种误认却反映了他们思想的真实。
对此,波特利指出,在事实和记忆之间的差异,最终提升了口述资料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它不是由错误的回忆引发的……而是由记忆和想象积极地和创造性地产生的,以便于努力理解重要的事件和更一般的历史。⑦
既然主观性和身体性是记忆的重要特征,那么,该如何把握它并资料化呢。在这方面,民俗学、人类学的访谈记录法,社会学、历史学的口述历史的方法等,都值得借鉴。关于访谈记录法的特征,日本民俗学家干叶德尔指出,访谈记录不仅关注叙述内容本身,还关注叙述人的视线、态度和真实的心理反应;通过时间轴的“现在”和空间轴的“现场”,构筑“过去”与“彼方”的历史记忆,并结合身体动作、表情等“非语言”表达方式,探求传承社会的“心意现象”。
而口述历史的记述方法,樱井厚提出了三种具体做法,即实证主义的方法、解释性的客观主义方法、对话式的结构主义方法。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是指重视讲述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追求讲述内容的规范性和前后一致性。而解释性的客观主义方法和对话式结构主义的方法则强调讲述人的主观性。解释性客观主义的方法通过归纳推理的方法解释讲述的内容,将生活片段多重叠加排比描绘出生活中的规范和制度的现实存在。这个手法的一个特点是收集生活片段史加以分析和解释。与实证主义方法相同的一点是,两者都具有追求客观事实的指向。对话式结构主义的方法认为,讲述是讲述者和访谈者之间的互动形成的,关注讲述行为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由于有研究者的加入,使得采访者和讲述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⑧不难看出,在对记忆的主观性和身体性的把握上,第三种对话式结构主义的方法最为有效。
德国民俗学家雷曼(Albrecht lehmann)通过口述历史的研究,开发出通过日常话语的“意识分析”方法,分析出个体记忆如何通过社会文化的多种作用而被定型化和表象化。所谓“意识分析”,侧重分析个人的历史、环境的历史、宏大历史是如何在个人层面被体验、被理解的。在揭示这个过程中文化是如何从发生条件的角度给以说明的时候,提供历史的证据。意识分析最重要的材料是自传资料,这些资料是在质性社会调查的原则下,将人与人、或小组访谈对话中记录下来的。有时文字记录比如日记信件的分析、照片等物质文化,也成为分析的对象。
意识分析的方法具体如下:先将大量的口述资料彻底地文字化;与此同时,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包括创作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各种公文书、绘画、照片、报刊等资料作系统的调查收集整理,找出相关的内容,保存进电脑或卡片。然后对口述调查中所出现的重要的意念、表象、知识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来源。通过这样的操作,可以析出千百个日常个体记忆中共通的表象构造,进而可以找出社会记忆形成的内在机理和逻辑。⑨
三、避免记忆研究的平板化、定型化
近三十年来,在诺拉的“记忆之场”研究范式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类似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通过对某个纪念物、纪念馆、纪念空间的建造、资金来源、建造宗旨以及变迁作详细的考察,来分析其作为纪念空间的意义。再加之时间的要素,来描述在这个纪念空间举行的纪念活动,来挖掘记忆在不同时代不断被重构的过程和记忆的流动性。这些研究往往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塑造共同的历史想象的可视性表象的、文化的、政治的行为相联系,成为解读近代历史中文化建构的一把钥匙。诚然,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大量的事例的挖掘,会给人们展现出一个丰富的社会场景,扩大记忆研究理论的解释力,并且从中发现不同国家地区的特性与共性。但是,如果研究仅仅在这个层面上平面铺开,满足于事例量的增加,会导致记忆研究的平板化和类型化。
要深化记忆的研究,重要的是要把握记忆的本质特征。既然记忆具有感性的、身体的、主观的特征,那么,就很难用过去固有的社会科学的对其进行分析性的把握,而有必要将调查对象作为一个复合的整体来看待。其可能的相关概念包括:想象、身体、感觉、感性、行为、直观、经验、空间等。将记忆的事实与上述关键词相关连,通过概念化的作业,开拓出记忆研究的新方法。与此同时,对那些边缘性的、被抹消的记忆,以及被格式化的记忆的分析,也应该成为记忆研究关注的对象。
一个社会通常有一个代表主流价值观念的记忆规范,公共记忆在形成过程中通常要通过规范过滤那些“有害的、特殊的、少数的”记忆。例如,在日本静冈县热海市,有一块为七个甲级战犯竖立的“七士之碑”。在接受东京审判结果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格局下,这个纪念战犯的记忆表象所代表的记忆无疑是边缘性的;但是,它所代表的日本社会同情战犯、否定东京审判的一股暗流却是不可忽视的。近年来,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心理基础就在于此。这个现象与日本旧军人记忆战争的身体性有直接的关系。发掘、分析这些边缘的记忆,可以帮助人们更为全面了解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的构造。
记忆的另一面是忘却。权力的交替,社会的变迁、文化导向的转移,都会导致某些记忆被抹消或忘却。这些政治性的文化操作,很多反映在记忆的表象物的变迁上。例如,广州黄花岗公园石碑上被凿掉后来又被复原的人名,全国各地被推倒毁坏的纪念碑,博物馆的展览内容的改变,都是历史记忆被抹消的见证。分析、总结、揭示这些现象,都应该成为记忆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记忆的格式化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笔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抗日战争记忆的时候,发现经历过战争的七八十岁的老人的战争记忆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个性。他们讲述的当年日本军队在村落里的状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日本军人的印象。从他们的叙述中,日本军队的侵略事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例如,一个老人讲到住在他家的日本军排长“渡边胡子”,曾经在他家里烹饪从别的村民家抢来的鸭子;还有,老人说日本军队强迫村民挑担,按照年龄增加重量,50岁的人挑50斤、70岁的人挑70斤等,故意欺负年纪大的人。还有人提到日本战败时的一个细节,这个“渡边胡子”抽出东洋刀,狠狠地在他家的房柱上砍了三刀,然后哀叹说:“我们大日本帝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可是,到了广西就日落西山了。我们不该来广西。”
但是,这些老人的后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通常只会用“烧、杀、掠、抢”这样抽象的词汇来描述日本军队在村落的情况,很少有具体的细节。不难理解,他们的日本记忆,已经逐渐被教科书、电影等格式化了,失去了原有的多样性和个性,而与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日本印象一致。个体记忆在形成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更进一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公共记忆的时候,这样的格式化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过程和机制,却是记忆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注释:
①[日]若尾祐司、和田光弘编著:《歴史の埸——史跡·記念碑·記憶》,東京,ミネルヴア書房,2010。
②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第158—17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③④⑤[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169、171、171页,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⑥[日]樱井厚《ィンタビュ一の社会学ライフスト一リ一の聞き方》,第9页,東京,セリカ書房,2002。
⑦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⑧[日]樱井厚《ィンタビュ一の社会学ライフスト一リ一の聞き方》,第9页。
⑨《日本民俗学》(263),第31—56页,日本民俗学会,2010。
作者简介:王晓葵(1964— ),男,河北省文安县人,名古屋大学学术博士,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多文化共生研究所共同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田粉红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上一篇:记忆与历史理解
下一篇:也谈社会史研究的“碎化”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