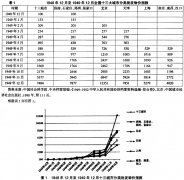记忆与历史理解
“记忆”这一术语在当今得到了广泛和有争议的传播。它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性和真相有着特别夙求的特权话语,不仅进入到史学领域,也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是,与记忆相关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历史理解有何教益?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对于我们的记忆又有何教益?
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在追求普遍性和特殊的认同夙求之间徘徊不定。①这一点似乎是一切如实记述的历史所具有的不能解决的纠结的一个表现。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普遍性维度植根于历史学家对一套方法的追求中,这些方法旨在使获得合理历史解释的机会最大化,使错误的机会最小化。由于历史特殊论经常在记忆的语言中得到表达,历史与记忆之间便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历史”是作为一种凌驾于特殊记忆之上的伪客观性话语而出现的,它宣称具有一种经验上的实在和历史所缺乏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记忆是作为一种不可度量的话语而出现的,它服务于欲望,要求拥有自己的不能被证实的合法性。面对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历史学家将持何种态度?本文将对这种关系的某些显著特征进行考察,但并不意欲解决问题,而是指出捷径之所在。
当前,在“记忆”所表达和确认的事物亦即主体性的需要与对证据的需要之间,存在一种可悲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冲突。而在今天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乃至研究领域有着一种文学批评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称之为“不再重视证据的认识论反而去强调对证据的欲望”的冲动。②这里的“对证据的欲望”指的是,人们不必去追求一种观点在实际中的真实性,而只是希望它是真实的,以便有机会去支持或攻击这种观点。显然,证据绝不会客观地为自己说话:它总是在一个由多个主体建立的论辩背景中,从主观的立场上去说给其他主体听。简言之,没有“纯粹”证据这样的事物。此外,对证据的欲望必然是更大结构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因为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建构或重构过去的冲动——兰克、米什莱、布克哈特等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正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如果不对欲望有所遏制,人们所设想的过去就只会变成主体性所想象的过去的一个投影。但根本说来,我们从这种做法中什么也学习不到:只有对主体性有所遏制,它才能学会让自身参与到与之对立的主体性中,参与到主体性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和物质世界中。
让我们换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认为我们应当记住过去是很容易的,但我们并不能记住过去,我们记住的只是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记住”的是现在依然存留于我们情境中的东西。所谓我们思考过去,意思是我们以某些批判方法为基础去建构或重构过去。与之相关的格言应当是“记住现在,思考过去”。魁北克的官方格言“Je me souviens”(英文为I remember,意思是我牢记在心)涉及的就是当下的主体性,不是被思考的过去。③当历史理解被描述为“记住”时,我们可以推断,我们正面对一种提升当下某种可能令人满意的集体认同的尝试。这一点几乎是不变的。
不假思索地摒弃主体性是很容易的,但也是完全错误的。而声称拥有绝对客观性的视角则是不能被证实的。但是,将历史仅仅变成当下为认同而战的衍生物同样是错误的。近来的历史哲学著作对历史理解给予了许多严肃思考,这些思考虽然没有解决与特定认同相联系的主体性的需要和对证据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但还是对这种冲突进行了定位。就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而言,近来的历史哲学著作中有两种对比鲜明的趋势。一种趋势在柯林武德和保罗·利科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另一种趋势则在海登·怀特和米歇尔·德塞托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第一种趋势认为过去从根本上来说是可知的。这一趋势出现在利科的在一种综合中涵盖各种异质现象的历史叙事观念中,利科称之为“异质综合”(synthesis of the heterogeneous)。④不过,这一趋势在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特别是在“历史的证据”这一节中,得到了更为明显的表达,该节几乎一半篇幅是用来讨论“谁杀死了约翰·道埃”这个问题的。⑤柯林武德用一种侦探小说的风格详细叙述了詹金斯探长对修道院院长隔壁邻居约翰·道埃谋杀案的调查。调查在发现院长本人就是凶手中达到顶峰。多年以来,道埃一直在秘密敲诈院长,威胁说要公布院长死去的妻子在多年前,也就是刚刚结婚前的一次越轨行为。道埃的敲诈吸干了院长全部私人财产,现在他又想得到院长已故妻子的那份定期存款,那是她托付给院长以备女儿结婚之用的。当院长看出探长正在逼近他时,就服用了氰化物并瞒过了行刑人。
柯林武德对解决约翰·道埃谋杀案的记述(他将之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范例)是以一种明显的缺失为特征的。他完全忽视了给院长和院长一家带来巨大痛苦的创伤(trauma)。很明显,本案中的痛苦和隐情是非比寻常的。在院长为敲诈而付钱的整个期间,他都不知道那个引诱他妻子的人正是敲诈者本人。他的妻子可能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在支付勒索以保护她。同样,他那婚后六个月出生的女儿也不知道她的生父不是院长而是约翰·道埃。柯林武德对院长与其死去的妻子、院长与其女儿,死去的妻子与邻居之间等等极度痛苦的关系根本不感兴趣。简言之,他将这个家庭全部的文化史抛诸一旁。柯林武德实际上并不认为创伤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完全将创伤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
柯林武德将历史性的过去描述成某种由遵循历史研究法则的历史学家所建构的东西。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研究只能产生一种真实而客观的结论。柯林武德确实宣称,历史论证应当“不可避免地跟着证据而来”,它证明了它的论点“就像数学中的证明一样是结论性的”,但这完全是错误的。⑥同样,对探长来说,只有一个故事对谋杀案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一旦他发现了这个故事,他就会完全自信地坚持它的真实性。但对历史学家式的侦探来说,只有将所有与创伤相关的事物排除在外,他才能得出这种确信。
历史哲学中的第二种趋势认为过去是不可知的。德塞托在《书写历史》中坚持认为,与死亡和他者的对抗是西方现代史学出现的关键。他认为,对将要被书写的历史而言,过去和现在之间一定有一种断裂。他还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有义务去承认那些它不能理解的东西——无法弥合的分歧和缺失,也有义务去承认那种尽管很难但仍要去努力表现的他异性。⑦对海登·怀特来说,真实的历史不可更改地以崇高为特征——也就是说,以那些过于恐怖而不为人所知的事物为特征。海登·怀特与柯林武德所坚持的历史学家在其头脑中重演过去完全不同,他对过去当中太恐怖而无法被重构的事物留有余地。正如怀特指出的,那些受到错误引导的“美化”过去的尝试“使历史丧失了那种无意义,单凭这种无意义就可以刺激活着的人去创造对他们自己及其后代来说全然不同的生活,也就是说,赋予他们的生活某种只有他们自己可以负全责的意义”。⑧在怀特看来,“历史性本身既是一种实在也是一种神秘”⑨——这种神秘是无法回避的。换句话说,怀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本体——也就是说,一种关于历史知识限度的概念。
人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但却是相互关联的方式来思考这种历史本体。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历史本体可以被视作我们当前所知事物背后的一个不能被理解的地带。在此意义上,这种历史本体等同于一种史学撰述的谦恭原则。它与希罗多德的谦恭很相似,希罗多德经常重复由他的消息人讲述给他的故事,但却让自己与那种认为此处所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观点保持着距离。不过,怀特的观点只是与希罗多德的相似而非相同:因为他的这种历史本体观念暗示了,在这些故事、证据、记忆等类似的东西背后的确存在一种真相,尽管人们可能受到阻碍而不能认知它。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这种历史本体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个领域,它充满了:(1)创伤太多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物;(2)过于陌生而不能被当下理解的事物;(3)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不能被建构和重构的事物。
不能被理解的地带这一观念提出了另外一种处于记忆与历史背后的视野,它能够帮助我们阐明记忆与历史之间棘手的关系。认为记忆与历史彼此勾连是错误的,比如,认为记忆是历史的原材料。同样,认为历史仅仅是所有可能之记忆的总和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托尔斯泰先生,将所有记忆组合在一起是不能重建滑铁卢战役的。但是,认为历史与记忆只是彼此对立同样是错误的。一方面,记忆远不是历史的原材料,记忆是时常萦绕在历史之上的一个他者。记忆是当下的主体所建构的过去的影像。因而,记忆在定义上是主体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和前后矛盾的。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有义务成为客观的、统一的、有规则的和合理的。然而,历史不能完全如此,因为在已知的背后总有不可理解的残余,总有无法消除的主体性的参与。
凭借“上帝已死”的宣言,现代主义者尼采试图勾勒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尼采的意思似乎是说现代性已然成功或即将成功,因为现代性将自身从他者,即信仰、天启、玄学、超然性等其他理性的对立面中分离了出来。不过,尼采在一句经常被忽略的话中也承认了排斥他者所引发的焦虑:“我们怎么才能安慰自己,这凶手中的凶手?”⑩在某种程度上,记忆的出现或许是对现代性的失败所导致的焦虑的回应,因为记忆的重点在于求新,它为依然萦绕于当下的过去之物提供了足够的记述。
比如,可以思考一下历史这门有着西方、基督教和一神论根源的学科,与它的一个他者,即那些不属于“西方”之一部分的世界和经验的关系。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指出,历史学家所记述的非西方的历史“通常是一部史前的、原始的和前科学的历史”,它“只有一种选择——将非历史带入历史”。南迪认为,这类历史的目的“完全是在一个精心表达的参照系基础上,彻底剥去过去的外衣”。这种关于过去的观念,当然是十足的柯林武德式的。南迪继续说到,“启蒙运动的敏感……假设了历史与对过去的建构之间是完全均等的;它还假设了历史之外没有过去”。(11)在这种意义上,非西方人的集体记忆就变成历史的他者,被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
但在实际上,这个他者却非常接近历史,或至少非常接近历史学家。南亚“庶民学派”的一位历史学家迪皮什·查克拉巴蒂,曾经指出庶民是如何进入到西方化的中产阶级自身的形成当中来的。这些来自庶民阶级的人民以奴仆这一实体出现在中产阶级的家庭和空间中,并因此成为中产阶级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经验已经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到史学撰述之中。印度中产阶级里的许多人在还是孩童的时候,就遭遇过庶民那令人着魔的故事,这些故事对这个世界作出了解释并提供了对它的全面理解。南亚庶民阶级的集体记忆虽然是作为与历史对立的他者而出现的,但这个他者却是南亚历史学家在他们成年时可能非常希望理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记忆是历史的他者,我们也必须承认历史是记忆的他者。记忆提出的诉求只是有可能真实。在对证据的需要上,历史与记忆是尖锐对立的。历史提醒记忆需要来自目击证人和存留之物的证据。记忆虽说是不明之域:它不能被信赖。但人们不应由此就认为历史是光明之域,因为在历史的相对光明和记忆的相对黑暗之外,我们必须承认还有一个巨大的关于历史的不可知领域。这一经验来自我们时代认同的不确定性,因为在削弱下述观念即存在一种我们可以接近的唯一的权威视角时,认同的不确定性也削弱了历史与记忆的傲慢:一方面是确定性的傲慢,另一方面是真实性的傲慢。
历史与记忆的界限或许在20世纪一个重要的现象中得到了最为清楚的表达,那就是对所谓犯下国家支持的暴行罪的罪犯的审判,审判的目的是既要达到真理和正义,又要通过形成集体记忆以帮助塑造新的集体认同。人们为审判所构想的这种双重计划,其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同时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它怎样才能做到?又怎样无法做到?那些在同时为发现历史真相和重构集体认同而努力的法院和军事法庭都与当下的语境相关,这种语境表现的是某些普遍的理论要点。我试着将这些理论要点以命题的形式表达如下:(1)历史、认同和记忆的不确定性是相互的;(2)历史与记忆截然不同,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不同民族或群体所“记住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中;(3)尽管如此,历史与记忆的界限却不能得到精准的划分;(4)缺少一种唯一的和无可非议的权威或架构,就不能解决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时代,历史的在场意味着历史能够永远征服记忆:也就是说大写的历史(History)吞噬了“各种小写的历史”(histories)。而在一个宏大叙事崩溃的时代,就不会如此。所以,我们很难知道怎样才能克服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记忆的总和并不等于历史。我们同样能够确定的是,历史本身并不能产生一种集体意识,也不能产生一种认同,当历史被用于认同形成和认同提升的计划中时,麻烦就会来到。因此,历史与记忆之间依然存在着一条界限,我们可以时不时地穿越其间,但我们却不能也不应希望消除它。我们时代更让人烦恼的趋势或许是以可信的记忆去消除压抑的历史。但是,如果真理和正义(或它们留给我们的无论何种幻影)对人们还有所要求的话,它们至少还需要大写历史的幽灵。否则,留给我们的就只是此刻感到美好的东西,或用来去满足邪恶的东西。
注释:
①Eric W. Hobsbawm, “The Historian between the Quest for the Universal and the Quest for Identity”, Diogenes, Vol. 42, Issue 168(December, 1994), pp. 51-64.
②Eve Kosofsky Sedgwick, “Against Epistemology”, in James Chandler, et al. eds. , Questions of Evidence: Proof, Practice, and Persuasion across the Discipli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136.
③“Je me souviens”这句格言来自一首诗的第一句,后面两句是“生于百合底,长在玫瑰下”。百合与玫瑰分别象征着法国和英国。这句格言就是让加拿大魁北克的居民牢记他们的现在。——译者
④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ix.
⑤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ed. W. J. van der Duss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66.
⑥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 262, 268.
⑦Michel de 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 T. Conl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xxv-xxvi, 5, 39, 46-7, 85, 94, 99-102, 218-26, 246-8, and passim.
⑧Hayden White,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2.
⑨Hayden White, “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53.
⑩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with a Prelude in Rhymes and an Appendix of Songs,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 181.
(11)Ashis Nandy, “History's Forgotten Double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2, Theme issue 34: World Historians and their Critics(May, 1995), pp. 44, 47-48, 53.
作者简介:阿兰·梅吉尔,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田粉红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上一篇:功力、视野、理论
下一篇:“记忆”研究的可能性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