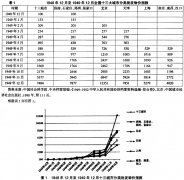身份转换中的生活重塑
内容提要:1950年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所有制变革,同时内含将资本家由“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目标诉求。本文通过梳理资本家改造对其劳动生活、物质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的影响,尝试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体味政治与生活关联的生成过程。文章认为,资本家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身份转换,不仅意味着个人改造的完成,更是对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生活重塑的实现。
关 键 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资本家 身份转换 日常生活
作者简介:满永,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
1955年11月,刘少奇谈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对资本家的影响时指出,“要改变他们的所有制,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因此,他们动荡不安,感觉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不晓得明天怎么样”①。显然,在刘少奇看来,工商业改造是所有制的变革,更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的重塑。1956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也强调,“为着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必须采取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就是说,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组织资本家的学习。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②。由“剥削者”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身份转换,意味着这场改造运动是体制变革与人的再造同步。与所有制变革不同,资本家的身份转换,要在教育学习的基础上促其生活方式与习惯的转型,也唯有在日常生活的重塑中,始能触摸“人”之改造的历史脉搏。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中的关键性影响,是1950年代中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总体来看,以往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新政权建国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及政策选择,基本上是一种宏观的政策史描述③。再就是受微观分析视角的影响,不少研究开始从地方层面解读政策实践及其社会效应,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对资本家心态变化的分析,使我们得以聆听到政治运动中人的声音④。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心态变化的研究多是对资本家心路历程的从疑惧到恐慌再到服从这样三阶段的描述,但对心态变化的深层原因未深究。如前述刘少奇所言,改造中资本家的情绪不安,虽有所有制变革的原因,但同样受到因此带来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变化之影响,而这一生活变化的内容在既有研究中鲜有触及⑤。事实上,资本家的心态变化一方面是出于对政策的反应,但主要还是政策实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及习惯。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注,不应仅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还要深入社会日常生活场景,来理解政策对受众生活的影响。
从生活变化的角度观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至少在三个方面对资本家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又与其从“剥削者”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身份转换相关联。对资本家而言,由原来的企业主到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身份转换,首先带来的是日常劳动生活的改变;而收入由“利润”到“定息”和薪金的转变,同样会影响到他们的物质生活;在劳动和物质收入同时改变的前提下,家属的身份同样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的则是整个家庭生活的改变。经由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重塑,资本家最终实现了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身份转换。
一、“企业主”到“资方人员”:身份转换中的劳动生活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谈到改造对资本家身份的影响时指出,“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⑥。同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会议上的讲话中,也从身份转换的角度阐述了改造的意义:“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也是改造资本家个人的过程。阶级消灭,个人改造,最后都变成工人,得到一个愉快的前途”⑦。显然,就毛、周的认识看,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并非简单的阶级消灭,而是身份转换。在由资产阶级到工人阶级的身份转换中,首先发生变化的就是劳动状态。在企业公私合营过程中,政府对原有实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但包下来并不意味着其职位和工作内容保持不变。1954年政务院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但也同时强调了,“在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⑧。“量材使用”的原则虽保障了原有人员的工作,但工作职位的重新调整势必带来劳动内容的变化。在私营企业里,原有人员尤其是企业主,是企业的领导者,但在“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之后,无论职位如何安排,附属地位应是确定无疑的。
在地方的改造实践中,资方实职人员多数均按“量材使用”原则重新安排工作。广东省6市、23县的调查发现,截至1956年4月,资方实职人员16434人(资本家12034人,家属4400人)已全部包下来;已安排新职的11395人,占资方实职人员总数69.36%,其中任专业公司经理60人、经理(厂长)981人,门市部(车间主任)1211人、科(股)长353人、工程师1人、一般技术员249人、一般营业员6574人、其他1966人。从9775个资方实职人员安排后职位的变动情况看,是“中间大、两头小”,提任的1039人,占总人数10.6%,维持原职的6965人,占总人数71.3%,降职的1771人,占总人数18.1%(潮州市42.6%)⑨。这份调查虽强调了安排结果是“中间大、两头小”,但从超过一半的人成为一般营业员可推测,应该还是有不少人从业主变为普通工作人员,这在人数居多的中小业主中尤为普遍。在江门市屠宰业中,资方90人中安排为门市部主任以上职务者仅14人,其余全部安排为一般从业人员⑩。对多数人而言,由业主到一般从业人员的身份转换,劳动内容与劳动自主性都会发生变化。如江门国民旅店资方从业人员xxx(档案原文如此)1955年因业务困难,劳资双方协议暂时离职,等业务好转再复职,但直至1956年4月仍未复职,并出现生活困难(11)。此情形突显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劳动自主性打了很大折扣。自主性的丧失,即便那些未被协议离职者,亦很难适应。在广东梅县,有些小商贩认为“组织起来不好,甚至不愿调国合部门,自贯彻保证自负盈亏的小商贩合理收入后,有的认为代销有困难政府会解决,收入好,过自由,相反认为组织起来收入少,不自由。因此不合条件的也积极要求分散经营,批不准则闹情绪,影响工作,有的上调国合不愿意去,认为国合工作多时间长又要下乡,既没电灯又没电影看,生活不习惯,照顾家庭不方便,不如搞代销好,甚至有的已调到国营公司的小商贩擅自跑回去并对别人说工作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了就会调国营”(12)。梅县小贩们对“自由”的反复强调,显然是出于对合营后“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改变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合营将他们的劳动方式由“个体”变成了“集体”,从而降低了劳动中的自主性。
小贩们的不适应主要源于身份转变中劳动自由度降低的苦恼,与他们相比,那些原本就工作在企业里的人应该更能适应合营后的劳动状态。但事实却不乐观。因为即便保留了职位的资方人员,在合营之后,同样面临在日常劳动中如何处理公私关系的问题。浙江省工业厅1956年9月在合营厂矿公方代表座谈会上就发现,合营厂矿中的公私共事关系,“好的仅占少数;关系很不好的也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厂矿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关系不够正常”(13)。毛泽东1956年在与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曾指,受“三反”、“五反”影响,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往往对私方代表相当警惕,因此影响了企业内的公私共事关系(14)。多数公方代表为了站稳立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力求与私方代表保持距离,一般“对私方意见则怀疑别有企图,怕钻空子,有的厂公方厂长出外开会,不叫私方厂长代行职权,却把工作、文件、印章全部委托计划科长代理”(15)。这里的处处提防还算是一种安全策略,广东梅县一些厂矿的做法则近乎刁难。“有的厂私方技术人员每天工作了13—14小时,不但得不到公方的体贴,相反给私方扣上了一个帽子是‘改造’,因此使私方人员说正如劳改一样,请求回家生产。还有的私方干部合营后降低了工资,由原来30元降为26元均未得到解决,其次还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要求调整”(16)。由于统战的压力,相信梅县的情形不会是主流,广东省在汕头等地的调查也发现,公私共事关系中多数表现一般,比较正常与不太正常者均属少数(17)。
受“三反”、“五反”影响的不仅是公方代表,作为私方代表的资本家对刚刚过去的运动同样心有余悸。毛泽东1956年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时,就指出“三反五反”斗争“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18)。杨奎松对上海“五反”的研究表明,运动之后,“资本家多半已很难自主指挥和管理生产了”(19)。资本家管理权的丧失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及工人监督权的提升,另一方面,经过运动冲击,不少资本家对未来不抱信心。济南的崔永和就流露了此心迹,“在此心情下,就越抬不起头来,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认为资产阶级‘百无一是’愧不如人,特别是因为自己具有历史包袱和阶级出身所限,心中顾虑更多,自己把自己看作是垃圾箱内的废物和毒药,对自己宣布绝望,认为此生已矣”(20)。有了这样的情绪,在后来的公私合营浪潮中,虽然资方实职人员均得到了安排,但既有教训也警醒他们应对自己的新职位有清醒认识。由此,原本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资方人员,在新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作内容日渐流于形式。
资方人员劳动内容的形式化,既有公方代表的提防,也有其主动撒手的原因。江苏苏纶纺织私方厂长的清闲就有着这两重因素,“刚合营的时候,公方私方厂长一般都有分工。但是在日常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工作仍然是由公方厂长负责。私方副厂长既没有主动去找工作做,也无人找上门。文件呢?重要的一些不该秘密的也当了密件,他们看不到,一般的或者下级的请示报告,都在办公室主任(党员)手上解决了,他们也插不上手。这样,私方副厂长只好坐‘冷板凳’,和茶杯‘打交道’了”(21)。汕头文化用品公司二联厂资方人员的表现,显然是吸取了“五反”运动的教训。“汕头市文化用品公司所属二联厂,不论资方或工人有事都向工会主席请假,资方虽是民管会主任,实际上是无权。不少厂的资方人员仍很怕工人,民管会开起来,不发表意见,工会主席说了就算。……不少资本家本身思想上还存在怀疑顾虑,不相信党的政策,怕犯错误,事事依赖公方”(22)。无论是苏纶厂的被动放权,还是汕头二联厂的主动弃权,伴随着“企业主”到“资方人员”的身份转换,资本家劳动内容与劳动方式的变化都是显见的。
二、“利润”到“定息”:物质生活之变
在1955年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陈云谈及改造对资本家物质生活的影响时指出,所有资方实职人员,“都安置起来,就要给他们饭吃。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还让他吃下去,我们并没有增加别的东西给他。他们的工资怎么办?一般地(不是所有的人)不降低。资方人员现在认为职业是有了,就怕降低工资,将来定息没有了,如果工资也少了,那是左右打耳光,两面夹攻”(23)。由陈云的这段讲话可见,资方人员的改造忧虑源于其对未来物质生活的担心。尽管陈云提出了“不降工资”、“给饭吃”的改造思路,但现实中所有制的变更对资本家的物质收入是有影响的。1953年李维汉给中央的调查报告《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对公司合营后的企业利润分配有如下建议,“关于利润处理,除提取少量公积金外,应保证私股分到一个最低限度的利润(可采用股息形式),但也应规定一个最高限度,其数可略优于银行存款利息,超过此数者不论多少应全部归于国家(即超额利润归国家),因为公私合营企业一般必有超额利润,而此利润之得来全是由于公股参加之结果”(24)。该方案保障了资方人员的利润收入,但也限制了其收入的额度。1954年政务院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将“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限定在企业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25)。1956年2月8日,国务院又通过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新规定将原来的浮动制利润分配方式固定下来,以年息“1厘到6厘”的固定比例支付股息。此举虽使资本家可以在不考虑企业生产情况的条件下,每年都能得到一定收入,但也使其收入不会再随着企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而改善。
无论是陈云的“不降工资”还是国务院的“定息”安排,均是希望在不影响资方收入的情况下推动改造进展。但在改造实践中,对私股利润的限制以及股息的固定化,还是使不少改造对象的总体收入有所降低。下表是山东省114户大型公私合营及私营工业在职资方人员1950-1955年收入变化情况:

上一篇: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
下一篇:七十五年来西路军研究述评(上)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