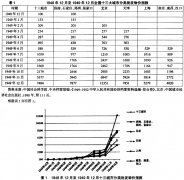中国国民党党团述论(1924—1949)
内容提要:中国国民党改组伊始,即在“非党团体”中设立秘密党团。党团服从所属各级党部领导,功能在于贯彻党的主义,巩固自身,争取同情,打击异己,吸收党员,以此掌控和引导非党机构和群众团体的活动。党团活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偏重青年学生组织和军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侧重民众团体和“民意机构”。建立党团的初衷是为推动国民革命,但与中共竞争群众运动领导权很快便成为党团活动的重要目的,后期针对性更强。党团组织在国民党内曾长期存在,并受到高层的高度重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独特性。
关 键 词:中国国民党 组织制度 党团 民众团体
作者简介: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所谓“党团”,如果不是“党”和“团”的合称(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一般是指“议会党团”,即由属于同一政党的议员组成、以统一本党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为目的的政党集团。议会党团是现代民主制度中的重要设计,其组织及活动均属公开。在中国近代史上,“党团”另有一个重要指称,即国共两党设置于非党机构和社会团体内的秘密组织。党团曾在国共两党早期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共党团于1945年“七大”后改为党组,其组织和运作公开化;国民党迁台后,党团作为秘密组织曾长期存在,但目前早已演变为议会制度下的公开组织。
国共两党几乎同时建立各自的党团组织,且均是对俄共相关制度的摹仿。由于党团组织及其运作的秘密性,对于曾经作为两党重要制度的党团,学界研究非常有限。关于中共党团在各个时期的组织状况及活动情形,近年来有若干论文发表,①虽然还比较粗略,但对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相对而言,对国民党党团的研究更为薄弱,②既有论述中亦有不少误解。如张玉法在全面论述中华民国时期人民团体发展演变的著作中,仅提及1940年10月“国民党中央将社会部改隶行政院,此后对人民团体之指导监督,不采取直接形式,而运用党团力量,以达成党在人民团体中之任务”,指出“此为国民党督导人民团体方式的重大改变”。③但国民党党团并不始于此时,其作用亦未发生质变。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一书中有一节内容讨论“党团的成立与作用”,但在总量极小的篇幅中又有近半内容叙述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党团,对于国民党党团,不仅语焉不详,而且不尽正确。如认为类似共产党的党团作用,“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内并不存在”,“从1927年夏开始,国民党终于开始了独自的党团活动”;1929年废除《党团组织通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制定新的党团组织法”;党团在1929年后消失,1938年临全大会后才意图恢复。④这些看法都不符合实际情况。魏文享在《国民党、农民与农会》一书中专设一节论述“农会中的‘党团’”,其实际内容则是各级农会组织中国民党党员的分布状况。⑤对于党团这一国民党组织史和民众运动史上的重大问题,既有论述对其制度形态的描述还不充分,对其实际运作和效用尚未涉及,对于党团制度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及意识形态因素缺乏讨论,资料也相对单一。本文试图以档案资料为重要依据,尽量在上述诸方面有所弥补和推进。由于党团的秘密性质以及制度形态与实际状况不尽相符的事实,有关党团实际运作的资料较难获取,本文的讨论仍然难称充分,敬请方家指正。
一、党团的组织形态
党团这一组织,不仅中国共产党取法俄共,对国民党而言同样是“以俄为师”的产物。据学者考证,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其最初的蓝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俄共(布)章程分12章66条,国民党总章分13章86条,内容均由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⑥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第十三章为“国民党党团”,具体规定如下:
第七十七条: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之非党团体,如工会、俱乐部、会社、商会、学校、市议会、县议会、省议会、国议会之内,本党党员须组织成国民党党团,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
第七十八条:在非党团体中,本党党团之行动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规定之。
第七十九条:党团须受所属党部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及管辖。例如国议会内之党团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及管辖;省议会内之党团受该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及管辖;俱乐部等团体内之党团受该地党部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及管辖。
第八十条:执行委员会与各党团间意见有不合时,须开联合会议解决之。不能解决时,得报告上级委员会决定。在未得上级委员会决定时,党团须执行所属党部执行委员会之决议。
……
第八十二条:党团内须选举职员,组织干部,执行党务。
第八十三条:所在活动之团体一切议题,须本本党政策政略,先在党团内讨论,以决定对各问题应取之方法。所定方法并在该团体议场上一致主张及表决。党团在所在活动之团体内,须有一致及严密之组织,各种意见可在党团秘密会议中发表;但对外须有一致之意见行动。如违反时,即作为违反党之纪律,须受党之处分。
第八十四条:党员在议会者,须先自具向议会辞职书,贮在所属党部执行委员会处。
如与党之纪律大有违反时,其辞职书即在党报上发表,并且须本人脱离该议会。
上述规定的要点在于:(1)在非党组织中广泛设立国民党党团;(2)组织党团的目的在于“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3)党团与所属党部执行委员会系从属关系,党团须受所属党部执行委员会的指挥及管辖;(4)党团内选举干部,执行党务;(5)党团的运作策略,是先在党团秘密会议中取得一致意见、对外意见和行动一律;(6)违反党团纪律须受处分。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修改,第十三章“国民党党团”仅有个别文字修改或表述次序调整,未见内容更改。条目调整为第八十至八十七条。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方针政策逐渐转轨,试图将其从“革命”力量导向“建设”力量。但这一转轨充满矛盾、分歧和争议,直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才基本完成转轨的过程。作为渗透非党机关、群众团体重要管道的党团组织,在国民党“清党”后曾有过短暂的停顿,但不久即恢复运行,其作用且越来越被强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制订庞大的民众训练计划。此时国民党虽成为执政党,但对民众组织除了公开的党政指导监管外,仍强调党员组成秘密党团在团体内部发挥作用,将党团的运用规定得更为细密。1928年,中央训练部制定《中国国民党党团党员训练实施纲领》,⑧注明为“本党党员训练必备秘本”,该文件如此定义党团的意义和作用:(1)扩大党的势力,使非党团体接受并实行党的主张;(2)指挥并监督非党团体的活动;(3)从非党团体中吸收革命的同志;(4)防止反动势力在非党团体中的滋长;(5)在敌对的非党团体中施行破坏的工作。此五项内容,除保证民众团体的充分“党化”之外,强调防止“反动势力”的滋长,破坏“敌对团体”的工作,敌、我、友划分清晰。这成为此后国民党党团工作的一贯方针。
根据这一“训练实施纲领”,党团的设置范围大为扩展。《国民党总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之非党团体内设置党团,列举对象包括工会、俱乐部、会社、商会、学校、市议会、县议会、省议会、国议会,而《中国国民党党团党员训练实施纲领》列举的对象则包括农人、工人、商人、学生团体,学术、宗教和教育团体,妇女团体,政、军、警各机关,俱乐部,医院及一切慈善和卫生机关,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著作人、新闻记者等公会,群众大会,各种会议,议会,海外华侨团体,国际团体及其他。除党组织自身外,无论军政学、农工商、国内外、常设临时,均置于“党团”的天罗地网中。
尽管直到1928年,国民党中央领导民众训练的部门仍试图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推动民众运动,但事实上,在“清党”之后的独特政治生态中,民众运动基本停摆,党团活动也“无形停止”。陈立夫将党团活动的停止归因于“在清党时,我们的党团公开攻击共党党团,在打倒他们之后,我们的党团也就愈趋公开了”。⑨党团暴露,或许是党团活动停止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执政后,与民众团体的关系面临重大调整。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对《中国国民党总章》进行再次修改,取消“党团”章,只在第二章“党部组织”加了一条关于党团的条文:“第十四条:本党在不能公开或半公开地方,于必要时得组织党团,其组织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之。”⑩此规定只允许党团设于“不能公开或半公开地方”,且须“必要”。不久,国民党中组部提出,海外党部“未公开或半公开者所在多有”,纷请制定党团组织章程,而之前的《党团组织通则》“合之现在情形,不无扞格”,向中央常务委员会请示办法。国民党中常会第50次会议决议,废止《党团组织通则》。(11)不过这并不等于党团制度的废止,党团组织和活动虽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有过中断,但中断时间并不长。
1931年9月,蒋介石设在南昌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曾上呈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份《中国国民党剿匪区域党团组织方案》,(12)规定党团组织“应于非党团体中以秘密活动扩大党的势力,集中党的力量,领导各界民众协助剿赤军事与地方善后之办理”,指向性明确。同时规定“各级党政委员会经调查所属之非党团体内有本党忠实党员五人以上者,须组织党团,其不及五人而认为确有组织党团之必要时,得指定具有该团体相当资格之党员加入其团体,以便组织党团,指挥其活动”,“各级党团设书记一人,由各该党政委员会指派之,但须得该党团大多数党员之承认”,党团书记可视情况获得部分或全部生活费补助。党团领导下的民众,在以下诸方面对党政军的“剿赤”工作予以协助:(1)组织输送队,担任军队输送等工作;(2)组织向导队,担任引导路线及传递消息等工作;(3)组织慰劳队,慰劳受伤官兵,激发士气;(4)组织宣传队,扩大反赤宣传;(5)组织侦探队,侦探匪情;(6)其他剿赤清乡善后等工作。
1932年8月,国民党中央对海员、铁路、邮务等“特种工会”的运用加以规范,内容分三部分,一“组织及指导”,二“训练之实施”,三“党团之运用”,强调“党团之运用尤属重要,各级团体内应以党团为核心而领导其活动,庶党的主义政策命令透过民众,使民众与党打成一片,而树立本党领导民众、完成国民革命之基础”。特种工会中的秘密党团承担下列任务:(1)扩大国民党在各特种工会中的组织;(2)将国民党的一切政策命令渗透到工人中,使工人与国民党打成一片;(3)防止其他一切政治团体在工人团体内活动;(4)在无形中领导并监督工人的活动与思想的倾向,并把握其中心分子;(5)在工人团体内取得重要职务,作为活动的中心;(6)吸收工人团体内的优秀分子;(7)随时将工人团体内各种情形及活动情形报告中央。(13)
上述两个方案中,党团的强势作为并不异于1928年的“党团党员训练实施纲领”,只是实施对象较为特别,一为“剿匪区域”,一为“特种工会”,可以视为“于必要时组织党团”原则的落实。但不久,国民党对党团重新作了整体性规定,再次将党团设置普遍化。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备案的《人民团体中党员组织工作通则》,对人民团体中的秘密党组织进行了统一规范,规定通过选举或者指定的方式产生党员核心“干事会”,领导团体内党员“实行党的运用”。干事会的产生方式是:各人民团体中的会员如有1/5以上为党员时,当地最高党部应将该团体中的全体党员秘密召集开会,选举3—5人组织干事会,负责指导其隶属团体中党员的活动,并由党部指定其中1人为书记;各人民团体会员中党员不满1/5时,当地最高党部应指定党员3—5人组织干事会,并指定其中1人为书记,主持该团体中党员的活动。若人民团体中没有国民党党员,当地最高党部应设法介绍该团体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或设法使该团体的负责人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干事会以不用名称为原则,必要时经当地最高党部之核准,得用各种可以公开的名称,如学术研究团体或俱乐部等。干事和书记为义务职。干事会的职务为:“(1)计划及指挥所属团体中党员之活动;(2)宣传本党之主义及政策;(3)吸收优秀分子加入本党;(4)侦察并制止反动分子之活动;(5)执行当地最高党部所指定之工作。”干事会至少每两星期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每月应将工作情形向当地最高党部报告一次;当地最高党部应依据上级党部所指示的方针,随时召集各人民团体中的干事及书记,指导其工作,并将其工作情形每月向上级党部报告一次。各人民团体中的党员对党部和干事会的决议及指导,须绝对服从,并严守秘密,如有泄漏或违背情事,一经查明,即由干事会呈请当地最高党部加以违反纪律之处分。(14)
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中,有“扩展关于各种社会事业之党的基本组织及尽量发展党员组织能力”的指示,“盖即所以发展党的运用于人民团体。本此原则,指示各地党部,除尽力推行社会事业外,并应指导人民团体中之党员,在其隶属团体之中秘密组织干事会,推动人民团体工作,以实现党的主义政纲;并从人民实际生活中以训练民众,建立党的信仰,实行党的作用”。(15)
国民党中央在1932年时显然已决定全面恢复党团的组织和活动,虽然上述文件中有的并未出现“党团”字样,但无疑干事会领导下的国民党秘密组织的活动方式与作用和“党团”完全一致,而且“党团”不久即再次频繁出现于有关民众团体的文件中,抗战前相关法规政策亦多有组织党团、干事会,以“实行党的运用”的规定。(16)
1940年,社会部由中央委员会直属改隶行政院,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指导由直接变为间接,党部不再有召集人民团体开会及训示之权,在民众团体内部起作用的党团遂更被着力强调。国民党中央认为,“自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主管民众组训以后,本党对于人民团体之关系,更有赖于党团之运用”。(17)希望今后各地党员在一般民众团体中,均应服从党团指导,发挥党的力量,贯彻党的主张,以达成团结民众,协助政府,推行法令之任务。国民党中组部在关于加强文化团体党组织及其活动的提案中指出:“今后为确立本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权,尤应运用党团作用,加强本党在人民团体内的组织与活动,一面以党的力量促进人民团体之发展与健全,一面使各种人民团体如众星之拱北辰,咸成为拥护本党实行主义之坚强的组织”,因此,“各种人民团体一律由所在地党部指导,其中党员组织党团,其尚无党员者,亦应多方访察其优秀分子,介绍入党,组织党团,以建立本党的领导权。党团负责人应督同所属党员,经常提携扶助非党员之优秀分子,并吸收其入党,以巩固本党的领导权”。(18)蒋介石甚至将党小组和党团是否健全作为考核党部成绩优劣的标准:“各级党部成绩之优劣,应以所属小组与党团是否确实编组,及其数量与质量如何为标准,考核工作必须切实执行”,中组部根据这一指示制订了工作计划,通饬各级党部在人民团体内建立党团组织,加强活动,并按月具报所属党团活动情形。为统一报告内容,便于考核,特制定各级党部党团工作月报表、党团成立报告表、党团所属党员团员名册,及人民团体概况表格各一种,颁发各级党部依式填报。(19)
此时关于人民团体内党员组织与活动指导事宜,由中组部成立党团指导委员会接管。中组部即拟具党团指导委员会组织规程,并指定委员组织成立,旋即依据五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加强人民团体内党的组织与活动案》决议,修订《中国国民党党团组织及活动通则》,督饬各级党部遵照办理,并将原设之民运小组,一律撤销。十次全会复将原来直属中央的全国性文化团体党团指导委员会撤销,关于各该团体党团之指导事宜,并归中组部党团指导委员会统一办理,据称“自兹以后,党团组织逐渐加强”。(20)
自1924年改组始,除1927—1930年短暂停顿外(其中1927—1928年,中央主管部门在理论上仍承认并试图扩大党团),大陆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一直存在党团秘密组织,1940年领导民众组织的主管部门(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之后,党团作用被进一步强调。就党团的组织形态而言,无论其与党部的从属关系,其秘密活动的方式,还是其巩固自身、拉拢中立、打击对手的工作作风,均一脉相承。
二、党团的实际运作
国民党“一大”后,党团相继建立,尤其在青年团体、学生团体中设置较多,在军队中也多有设立。
知识青年是国民革命的主导力量,青年学生又是知识青年的主体,因此,在学校和学生会中组织党团格外受到关注。1925年4月7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通告各学校党团主席,称因广州学生联合会改选在即,“希尅日招集贵校党团同志开预备选举讨论会,一致选举本党同志为要”。(21)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党团曾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该校党团于1925年11月19日到期改选,选出邹卓然等9人,请中执会备案,中执会令青年部核查。(22)一个中学的党团改选,需要上报中执委备案,可见党团的重要。(23)广州岭南大学学生党团的会议记录,透露了党团的活动情形。1925年11月30日,该校学生党团在岭南招待所开会,形成两个决议案:(1)预备于区分部开会时推选时任该校党团主席的周国杰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初选代表;(2)每周于星期一下午五时一刻开会。(24)不久之后的12月10日下午五时,该校党员李宝同、廖梦醒、林柏生等10人开会(另有3人缺席),先由林柏生解释党团组织法并陈说岭大学生党员有组织党团的必要:(1)招徕党员;(2)扩充势力;(3)宣传主义;(4)一致协助任职同志,使有后盾。再讨论组织问题,与会者一致同意“组织伊始不必复杂严密,只置主席秘书各一人即可”;“暂时可不必有章程,以免有形式之嫌,且人数太多,办事无事(原文如此)亦不必多所制限”;“关于党团名义,严守秘密,但其活动及个人活动可任使公开”。接着,进行职员选举,选李宝国为主席,廖梦醒为秘书。然后,会议讨论了工作分配问题、校内演讲问题、工界宣传问题、校内出版物问题,并一一指定负责人。最后确定费用分担原则。(25)该校学生党团的组织与党章的规定吻合,同时在组织构成、是否设置章程,以及具体活动方面有相当的机动性。
在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控制权的争夺中,党团的运作得到国民党重视。1926年7月23—31日,全国学联总会移至广州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有学者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特色,首先即在于系由国民政府及国民党补助经费、由青年部策划安排。出席代表54人,其中国民党党员42人。会前国民党即组织包括28位代表的党团,设立“党团干事会”,连续数次开会,决定会议人事安排,要求举凡“党内同志”提案,须先经青年部审查,再由党团干事会通过并提出。学总第八届代表大会后,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为确实掌握学总及学运动向,特别提出“全国学联总会工作计划案”,资助学总,津贴学总干部,以透过学总,达成学运之“党化”,亦即“以党团之组织,为有系统的联络,而间接受国民党之领导;使学生运动有了相当之统一计划,然后注意由学生团体去领导民众,而使民众革命化”。(26)
为掌握各校学生会领导权,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会同组织部制定《学生会党团组织条例》,并派专人到上海调查和指导全国学总会活动。青年部指示派往上海领导全国学总会工作的赵文涛,“会同学总会在上海各校学生会,从速进行党团组织,并会同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选派党团干事;务使各校学生会直接受学总会之指挥,间接则受本党之领导,而成为有系统之组织,然后团结各校学生会党团,一致应付学校当局,虽有各大学同志会之障碍,亦难撼动我青年联合战线于万一”。并让赵“特别注意”:“对于各校学生会或各地学联会之运动策略,务须使其无形中党化,务须组织强有力之党团为各该学生会之中坚,绝对不许党员在该校内有个人行动,以免为各该校当局所厄,而使本党青年运动之策略上生一线破裂。”党团须以团体的力量行动,各学生会党团须与学总会党团“一气相通”,各地学联会党团“务求统一联络”并且“务使与各地党部发生密切的关系”,使各地学联会“在表面上虽代表全国学总会宣传,在里面实为本党而努力”。(27)1926年,青年部制定《青年团体党团组织通则》,重申党团活动方法和纪律,规范党团行动,严格要求党团须谋定而动,行动一致,严守秘密,违反纪律将受到党部处罚。(28)
以上情况表明,国共合作时期学校和学生团体中的国民党党团,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不但有严格的组织条例和惩罚措施,其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9)
国民党一大党章列举的须设置党团的“秘密、公开或半公开之非党团体”,并未包括军队,但在国民革命时期,军队组织党团的情形似较为普遍。如“中央直辖山陕讨贼军党团最高干部执行委员会”主席路孝忱函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组织党团情形,并要求颁发党团图记,文曰“中国国民党山陕军党团最高干部执行委员会印”。(30)与此类似,中央执行委员会曾颁发“滇军党团最高干部执行委员会”木质印信一颗,文曰“中国国民党滇军党团最高干部执行委员会印”;(31)颁发“湘军党团最高干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木质印信一颗,文曰“中国国民党建国湘军党团最高干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印”。(32)
工人农民数量庞大,结构散漫,组织党团在技术上面临较多困难,但此时在工人团体中设置党团的文件亦见诸档案。相关文件规定,工人党团的活动受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直接指挥,其组织单位为小组(如铁路的小站、工厂工人的工作部门或班组、自由工人为俱乐部及寄宿舍、手工艺工人为工作店或寄宿舍等),每小组内设置一名干部,若小组数目过多,须设置若干总干部。(33)虽有此类规定,但实际设置恐怕较为困难。
此一时期,党团角色有时比较膨胀。1924年,广州各区党部全权代表会建议组织“党团军”,并制定《组织国民党党团军简章》,声称“以巩固后方为宗旨”,计划先由广州市着手组织,然后推行各属,经费由全体党员负担,枪械由政府发给或由党员筹款备价向政府请领,“总团部直接受大总理节制管辖”,下设联团、团、分团、小团,层层节制管辖。(34)中央秘书处答以“本党已在黄埔成立党军,无另设党团军之必要”。(35)1926年,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党团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询问其“有无指挥省立第一中学校行政之权,换言之,即敝党团能否指挥其活动区域之行政”。中央青年部复函指出“党团之性质,系在公开团体中作秘密之活动”,而“学校行政,系学校自身之组织,自有所属机关(如一中之于教育厅)指挥监督,毋庸党团搀越”。回函还提及,党团“因地位与需求不同,须分别组织,方能收效。如职教员须于教育会及教职员联合会或校长联合会中组织党团,学生须于校内校外之学生会中组织党团。该校党团未经分别组织,故一切活动,皆无依据,应即来部就商,以便指导”。(36)否定了学生党团将权力扩展到行政的意向,并指出其自身组织上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党团设置范围与前期相比有较大变化。1928年中央训练部制定的《中国国民党党团党员训练实施纲领》将党团设置范围扩大到极致,但这一文件不久即被废止,其规定未被执行,此一时期党团的设置范围基本限于“人民团体”和“民意机构”。
此时学校和军队一般不设置党团。如前所述,青年学生组织和军队是国共合作时期党团活动的主要领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中央对于学校和军队的党组织活动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抗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全国大学和专科学校中,可能只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几所学校设有区党部,一般院校未见设立。战前大学师生加入国民党者为数不多。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是抗战时期的事,尤其是朱家骅长主组织部时期(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曾把党务推进校园作为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举措。(37)军队党务工作在国民党“清党”之后实际上无法开展,1935年12月,军队各级党部被撤销,1939年3月虽恢复各级军队党部,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但正如论者所言,此恐怕“与全体不入没有太大差别”。(38)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复撤销学校党部和军队党部。
学校和军队党部组织的状况如此,由党部策动和领导的党团自然更不可能大肆组织和活动。事实上,即使在重新建立学校党部和军队党部时期,对秘密的党团组织仍有限制。1939年,社会部指示外派视察员如何组织学校党团:“凡各地未组织区分部之学校,该管省党部如已有计划尽速完成区分部者,即以团体方式从事活动,不必组织党团,但学生分子过于复杂,仍需组织党团,以资肆应,并须与各地省党部妥商办理。”如此,则组织党团为特例,在“学生分子过于复杂”的情况下才适用。(39)1941年又作了类似的指示:
……为此特规定凡学校内党员已达额定人数者,应即筹设区党分部,不必成立学校党团,其原有设有党团者,于区党分部成立后,应即取消,至各校教授会学生自治会及其他员生团体党团,应由学校区党分部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策动组织,并即由各该学校区党部主管,俾使就近指导,业经通函各省市党部查照办理。(40)
显然,是将建立公开的党部组织作为工作重心。同年,中央对“党团组织及活动通则”加以修正,对党团活动的范围加以限制:“党员团员在党务机关、三民主义青年团各级团队、军事学校、部队及其他经中央指定不许有党团之组织与活动之机关团体学校内不得有党团之组织与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依事实需要直接组织或解散或转令各级党部组织或解散任何机关团体学校内之党团,并得将省以下党部主管之党团改归中央主管,县市党部主管之党团改归省主管。”(41)国民党上层对在学生中运用秘密组织、让学生从事特务活动抱持戒备和反对态度。(42)但若学生组织跨校大规模活动,则希望通过党团加以控制。如“九一八”之后,上海各界抗日运动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其出席代表,各有背景,派别纷歧,明争暗斗,非常剧烈,该会为谋本党同志取得该会领导权起见,特派员前往指导代表中之本党同志,组织党团,统一其意志,集中其力量,指示其方法,俾能应付反动分子”。(43)
至于军队,恢复党部活动期间军人既集体入党,从常理推论,没有进行党团活动的必要。
在限制学校和军队党团活动的同时,“人民团体”内的党团组织被反复强调,除一般规定外,还常单独指令某类团体的党团组织。1939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商同中央宣传部,拟定《全国文化团体党团指导委员会组织条例》并提出委员人选:主任委员张道藩,副主任委员贺衷寒、潘公展,以“加强本党之领导”,蒋介石批准这一呈文。(44)妇运方面,“省市妇女运动委员会各委员负有推动当地妇女(运动)之责,对外以个人名义行动,对内则是党团行动,一切须受党的支配与指导”。(45)地方性民众团体中也强调党团作用。广东省党部制定的《调整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办法》,将“组织党团”作为“领导之加强”的重要内容:“在抗先总队中组织本党党团,于本届代表大会前成立,积极活动,务期在将来代表大会中取得决定性权力,在总队部下届职员中占得五分三席位,以后一切活动确切把握党的领导权。”(46)具体规定了党团的工作目标。
抗战时期,国民党上层特别强调在“民意机关”中设置党团。此时国民参政会和各省市临时参议会、县参议会相继成立,在“抗战建国”的大旗下,聚集了各党各派的知名人士和各界精英,显然,不可能用强硬手段逼迫他们贯彻国民党的意志,党团遂作为掌控“民意机关”的重要手段得到重视。1939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成立,“该会党团亟待组织”,社会部“除已密函中央组织部调查参议员中党员党籍外,并拟由中央委派洪兰友、李中襄、许孝炎三同志为该会党团指导员,俾策进行”。(47)中组部在答复广西省党部关于党团的三点疑义时指出:“……至各人民团体及民意机关,则应一律组织党团……如仅有团员而无党员,则应先策动团员参加,或吸收其中优秀分子入党,然后组织党团。”“各民意机关及各种人民团体中党员人数在五人以上者,亦应成立党团,不设区党分部。”(48)至1942年,“在民意机关方面,除国民参政会已组有党团,并由中央直接派员指导外,川、康……渝等十五省市之临时参议会已经成立党团,由各该省市党部予以指导。至其他省市或因省参议员均具有党籍,或因省参议会尚未成立,故均无党团组织。又凡成立县参议会之县分,均已饬由其所隶属之省党部转饬组织党团领导活动”。(49)
战后“制宪国大”召开之前,国民党中央仿照《国民参政会党团组织办法》,特别制定《国民大会党团组织办法》,对该会党团组织及活动作了详细规定: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9—15人组织党团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须“经总裁核定任命组织之”,“承总裁及常务委员会之命指导党团活动事宜”;党团指导委员会之下组织党团干事会,党团干事一部分由党员互推产生,其构成为:区域及职业方面31人(每一省市1人),自由职业团体方面6人(每一职业团体1人),特种选举方面25人(东北12省市各1人,西藏蒙古各1人,在外侨民5人,军队3人,妇女3人);另一部分为担任国民大会各分组委员会召集人的国民党党员,以及由中央指定的党团干事若干人(不超过由互推产生的党团干事的1/2)。党团干事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为召集人。党团干事会设书记一人,助理书记若干人,由召集人商定后呈请中央指派。干事会下设总务组、研究组、情报组,由书记提请召集人核准后由中央指派,各组工作人员由书记商请有关机关调用。党团干事会的任务如下:“(1)传达命令;(2)决定党团活动办法;(3)分配所属党员工作;(4)确保所属党员意志之统一与步骤之一致;(5)联络友党代表;(6)争取同情本党之代表;(7)调查各方活动情况。”国民大会党团下设宪法草案专门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前者由中央指定专家若干人(不限定代表)担任,“专门研究各党派对于宪法草案之意见,及本党应采取之对策,供指导委员会抉择,交党团干事会执行”;后者“由中央指定熟谙党派情形、富有会议斗争(原文如此)经验之同志(不限定代表)担任之,专门研究在国民大会中可能发生一切问题之分析与策划,供指导委员会抉择,交党团干事会执行。”国民大会党团干事会所属党员须切实执行命令,绝对保守秘密;为党服务任劳怨;牺牲小我,服从决议;捐弃成见,共同奋斗。否则将报请中央议处。(50)
以上内容足见国民大会党团干事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可以肯定,战时及战后,“民意机关”已经成为国民党党团活动的重心之一。“党团运用”甚至成为推举地方参议员的理由。1943年,组织部长朱家骅致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达西康省党部提出的该省参议员改选“特别希望圈定之名单”5人:高上佑、胡慕先、伍磷、麻倾翁、万胜蛟,请孔“察夺圈定”,以“便利今后党团运用”。(51)1946年浙江省参议会选举时未按上级意图选举该省党部原主任委员罗霞天为议长,现任主委张强胜出,事后有党员上告朱家骅,指责张违反党纪破坏组织,事实有二,一为“不遵从总裁及陈部长之指示”,二为“不召开党团会议”,即一面“高唱党内民主口号,又恐党团会议于己不利,故不惜破坏党团组织通则之规定,将总裁命令不交党团执行,又不督促召开会议”。(52)则不仅对其他党派运用党团,即使党内竞争,也须通过党团统一意志。国民党迁台之后,国民大会中的党团活动正规且经常,虽内涵已发生重大改变,但恐怕是倡行数十年的党团活动之最有形有质者,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论。
国民党对民众团体和民意机构中的秘密组织三致意焉,将之视作贯彻落实党的意志的保证,但对其成效并不乐观。
国民党高层对党团作用的评价并不高。长期在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陈立夫说:“我们的党团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那时中央组织部派出一些老而无活动能力的纯国民党党员在群众组织中工作,这些老党员当然没有办法与年轻而活跃的共产党员对抗。”(53)他说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情形。国民党设置党团并非学共产党而来,但国民党党团难敌共产党党团,确是实情。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并无其他党派的公开有力竞争,对党团组织又极为强调,结果却仍难如意。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对民众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经常自责,主管部门亦不时对之作出负面评价,如社会部曾指出因“党务技术”未受重视,“以致党的力量,无由充分表现,尤以对于党团活动及沦陷区域工作之推进未能因地因人因事制宜,利用各种机会,深植党的基础,殊为可惜”。(54)1947年,蒋介石在党团(三青团)合并时对国民党和三青团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中涉及党和团没有群众基础,对基层不发生作用等问题。他说:“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的内容,则是虚空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社会上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之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虑!”(55)蒋此处所说的“党和团”是国民党和三青团,非“党团”,但对党团的批评自然也包括在内,因为党团从事的就是基层工作,或者说,党主要是通过党团来实施对民众团体领导的,党团是党在“群众间社会上”发生作用的组织化渠道。没有基层组织,党团员在群众中不能发挥作用,正反映了党团的无效和无力。
但如果从数量上看,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党团组织有显著的增长。《人民团体中党员组织工作通则》于1933年1月26日颁发各省市及铁路党部后,据四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组织报告,“各地党部均已着手实施。凡各重要城市及铁路沿线之人民团体中,均已先后成立干事会,或其他核心组织,以资运用。其工作成绩最著者,为工人教育、合作事业,及吸收优秀分子等项”。(56)不过直到1940年前后,党团数量仍有限,尤其是在远离“重要城市及铁路沿线”的地方。如1939年,贵州全省仅有党团16个,此外,经中央社会部批准、用以代替党团作用的“民运小组”有30个,此时该省共有人民团体1841个,党团和民运小组相加,仅占民众团体数量的2.5%。(57)次年民众组织的归口管理机构社会部由国民党中央改隶行政院之后,国民党对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的领导更为间接,党团的作用也更为强调,即便如此,党团在人民团体内的设置并不普遍。据《中央党务公报》的数字,到1941年9月底止,各省各系统人民团体数量共25341个,党团总数为1220个。(58)党团数只占人民团体数的4.8%。不过,此后党团组织呈爆发式增长。兹将1941—1948年的党团数量及相应年份的人民团体数量对照列为下表,据此,党团占人民团体的比例,1942年后逐年提高,1945年已超过20%。

上一篇:谈谈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关系
下一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移民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