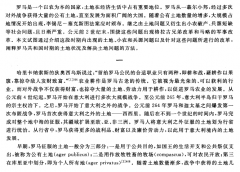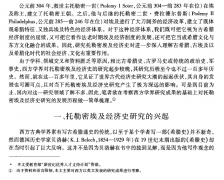古代世界无环境史的观点不可取
工业革命以来,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攫取所导致的环境危机,环境史研究开始兴起,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在环境史研究领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世界古代史领域基本不存在可供发掘和深入研究的环境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唯一一部现存的希腊化时代的游记——公元2世纪小亚细亚旅行家波桑尼阿斯的《希腊纪行》中,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希腊各地的历史掌故、建筑特色、神话传说等,却对当地的自然风光、河流山川、物产气候着墨甚少。这一材料择取标准与古代作家的世界观和古代游记体裁的写作传统有密切关联,但其对古代环境问题研究造成的阻碍作用却也是明显的。此外,古代史研究者试图借用环境史视角解释历史变迁所导致的牵强附会,也使得当代环境史学者对这门学科在古代史领域发展前景出言谨慎。古典时代阿提卡地区“环境退化”的假说,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反面案例。
古典时代阿提卡地区“地力耗竭”说的破产
在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盛行的年代,当西欧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人和普通游客前往雅典游历之际,现代阿提卡地区的光秃山丘与干旱环境让古典文明朝圣者们大失所望。他们无法将这个并不迷人的地貌景观同名扬地中海的雅典经济霸权与文化艺术成就联系起来。于是,水文侵蚀作用和过度放牧等因素破坏了阿提卡固有的宜居环境的假说迅速风行一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现当代环境史研究开始引起古典学者关注的情况下,古典时代阿提卡地区畜牧业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了当地植被环境,进而导致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希腊古典文明衰落的假说应运而生。英国学者瑟古德提出的偏颇观点便是这一思潮的集中反映。瑟古德宣称:“环境破坏是希腊的光荣所付出的代价。”根据持该观点的古典学者所提出的解释体系,雅典城邦本地经济生产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促使阿提卡居民过度开发周边原本丰富的畜牧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致使该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后出现水土流失、植被退化、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从而阻碍了雅典城邦与古典文明的持久发展。部分古典学家还通过对攸波利斯喜剧《山羊》残篇和柏拉图对话《克瑞提亚斯》断章取义式的附会而找到了支持该假说的“坚实”文献证据。
但是,严肃的考古学与地理学研究表明,近现代阿提卡地区相对贫瘠的自然面貌可一直追溯到史前时代,它并非雅典城邦缔造其辉煌古典文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解释雅典古典文明盛极而衰的“环境破坏说”在借助现当代环境史研究兴起的东风盛行一时后迅速偃旗息鼓,并且受到《堕落之海》等古代地中海生态史名著的严厉批判。
相比之下,用于解释古代世界政治、经济宏观走势的另外一些环境史假说似乎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相关例子包括降水量的变化导致4—5世纪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年平均气温的下降导致中世纪西欧与中国宋朝长期农业歉收等著名假说。然而,这些观点仅适用于宏观的粗线条论述,很难与充满偶然性的具体史实和客观历史演进历程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它们一方面容易引发知识界的兴趣与关注,另一方面则很难在正统史学的权威论述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上述种种活跃观点的提出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环境史学界关于“古代世界无环境史”的基本印象,而各种古代“环境问题”自身的合法性仍处于有待论证的处境之中。
古代环境史研究中的理想化与文化偏见
除宏观理论难以同具体史实相结合的困难外,由于古代环境史研究可资利用的优质史料极为匮乏,并且针对古代世界的环境史探索很难具备传统文献研究的考据性与当代生态环境研究的实验性,个别一度产生过轰动效应的相关成果事实上缺乏严肃的学术性,甚至可能产生混淆视听的消极效果。
例如,在古代地中海史研究中存在着借用环境史视角对伊斯兰文明进行理想化或肆意贬低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英国学者霍登和普赛尔指出,部分中世纪经济史学者关于伊斯兰教的向西扩张为地中海世界带来一场“农业革命”的观点在实质上是对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史料进行粗暴嫁接,从而人为构建伊斯兰农业文明理想化形象的做法。而年鉴学派史学家隆巴尔提出的荒谬观点——畜牧业过度经营和城市建设大兴土木所导致的木材资源短缺注定了伊斯兰世界将在近代早期同森林资源丰富的基督教世界竞争过程中遭到惨败——实质上是在貌似新颖的环境史视角下重构西方中心论的新瓶装旧酒把戏。可见,环境史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引入给世界古代史研究带来的并非只有新鲜活跃的“新史学”风气。由于古代环境史资料存在良莠不齐、量化程度较低、主观解释空间较大等问题,这项研究也为伪造史料和非学术观点的乱入以及个别持种族偏见的学者假借环境史研究之名重塑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为世界古代环境史研究提供启示
上一篇: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救济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