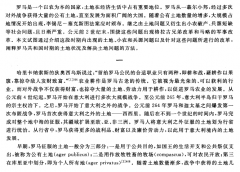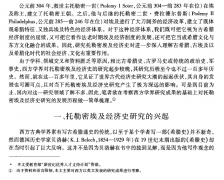公民参政思想变化新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参政思想浅析
【英文标题】The Civil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 Elites: Views on the Political Ideas of Italian Humanists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作者简介】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探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变化,折射出不同时期公民参政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对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尼、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解读,本文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充分反映民意的公民国家,对近代政治学的诞生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参政要求建立新型的政府,既能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秩序、又能为民众提供良好的生活。这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参政已经突破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模式和中世纪公民参政的传统,发展成为以建立近代政府为目标的、人民的政治运动。
【关 键 词】公民参政/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尼/马基雅维里
在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中,市民与王权结盟是建立近代国家的通常途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是工商业繁荣和市民阶级强大;二是缺乏能够统一整个意大利的王权;三是在城邦中掌权的不是封建贵族而是大商人、大金融家等新兴显贵,因此市民参政的作用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市民中产生出了一个由知识精英组成的公民阶层,其成员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政治,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所言:“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①
意大利的公民参政思想是很有特点的:首先,它是代表民意的,因为公民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其思想彰显出人民自下而上推动政治发展的意图。其次,它是近代的,因为与公民结盟的不是封建君主,而是像美第奇家族那样的城市显贵。第三,它是变化的,常常根据时局的发展,按照城市显贵与民众结盟关系的状况而变化。公民参政的思想,同知识精英想把传统的权力社会转变为反映民意的近代国家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
对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思想的研究,一般来说,是在两种解释体系的框架中进行的。第一个解释体系注重文艺复兴的“复兴”二字,强调公民参政思想与古希腊、古罗马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例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精英对罗马共和体制的推崇要高过对希腊雅典体制的推崇,因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常常是不稳定的”,而“古罗马与之不同,它形成的统治模式不仅把自由与美德结合到一起,而且把自由与市民的荣誉和军事力量结合到了一起。古罗马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把政治参与、荣誉与征服联系到一起,因而可以摧毁君主政体中形成的如下看法,即国王享有对其服从者的个人权威,只有国王才能保证法律、安全和权力的有效实施。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许多共和国来说,‘自由意味着摆脱暴君的专制权力,意味着公民通过参与政府管理其公共事务的权利’”②。
第二种解释体系强调的是公民参政的内容,例如:戴维·赫尔德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传统明确区分为两个共和主义流派,一个是“发展式”共和主义,另一个是“保护式”共和主义。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发展型共和主义理论家强调政治参与对作为人的公民发展的内在价值,而保护型共和主义理论家则强调它对于保护公民的目的和目标,即他们的人身自由的工具意义。发展型共和主义关心的是,它把政治参与和城邦的内在价值用作自我实现的手段,因为政治参与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内容。与此相反,保护型共和主义强调的是,如果仅仅依靠什么主要集团的政治参与,无论这个集团是人民,是贵族,还是君主,公民的美德面对腐败都是相当软弱无力的。因此,保护型共和主义理论家们强调认为,要想使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公民参与集体决策对于全体公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③ 与此类似的还有在学术界广泛流传的美国学者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和汉斯·巴伦(Hans Baron)提出的“马基雅维里式”公民概念与英国学者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发现的“西塞罗式”公民概念之争论,前者要求建立在法与正义之下的公民共同体,后者却以为公民德性能够在某一公正的君主之下得以实现④。
尽管上述研究经受了检验并在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的框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很清楚的是,它的许多方面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具体来说,公民参政的目标,与其说是要复兴古代的一种或两种的政治模式,毋宁说是要建立一种符合民意的近代国家,因此必须放到政治近代化的理论框架中来进行探索⑤。其次,我们得知,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的特点可以从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分析中得到解释。与政治学家不同,历史工作者更注重从不同时期的特殊背景中去分析公民参政思想的变化。这样,公民参政思想的演变就被看成是人们对于危机的一种反应,或者更为确切地说,通过对这些参政思想变化的历史研究,寻找出一种全新的、诠释欧洲近代政治发展潜在因素的分析方法。
这种公民参政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形式:从1300年到1375年为第一时期,特点是提倡美德和德治,提出建立德治社会的要求;从1375年到1450年为第二时期,特点是提倡公共利益,要求建立自由的公民共和国;从1450年到1530年为第三时期,其时君主制已在欧洲取得支配位置,出现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那样的著作。这里所说的道德论、自由公民论和君主论三种形式,虽然各有不同特点,但是,都是属于公民参政思想的范畴。这三种形式的出现,恰恰符合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期、发展期和转向期的特点。本文拟就这三个时期的顺序,分别说明公民参政思想的变化,以便了解当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治要求和对政治秩序的设计。
一、公民参政的历史背景
在14世纪的意大利,市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这要归功于城邦已经获得的两项胜利:第一,解除了外部的封建贵族对城邦的控制,实现了城邦的独立;第二,击败了封建贵族对城邦内部的控制,实现了城邦的自治。按照昆廷·斯金纳的解释,自由这个词,在文艺复兴时期作者那里,指的是“独立”和“共和自治”⑥。这种理解是从传统意义上说的,指意大利的城邦通过斗争,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约束,成为独立、自治的自由城邦。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劳罗·马丁尼(Laoro Martines)的说法,地理位置、2.5万至1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强大的资产阶级、一个被击败的贵族,已经成为工商业城邦主要特征和建立共和制城邦的基础⑦。因为城邦中绝大多数的市民都是自由民,而其时的资产阶级,也属于“民”这个范畴。从这种情况看,意大利的城邦可以说是人民的城邦,意大利的公民,也因此具有比欧洲其他地区更加优越的参政条件。
市民的强大,是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市民的人身是自由的,以银行家、资本家、商人、手工业者的身份从事着各种与商业、手工业有关的工作。据历史记载,在佛罗伦萨及其近郊,共有110个教堂、修道院和宗教组织,包括57个教区、5个男女合修的大修道院(每个有男女僧侣各80名)、24个女修道院共有女修士500人、10个僧侣会,30个教会医院,共有1000张病床,还有250至300个主牧师。在佛罗伦萨呢绒商会管理下的工厂多达300多个,在1346年时下降为200个,即使这样,这200个工厂共生产7000至8000匹呢绒,总价值达120万弗罗林金币。大约有3万人依靠呢绒业维持生计。该城经营其他布匹进出口业务的商会有20多个,每年直接经手的布匹达1万匹,价值30万弗罗林。这些布匹都在佛罗伦萨销售,还不包括那些在佛罗伦萨转销的布匹。在佛罗伦萨有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80多家。每年的营业额在35万至40万弗罗林之间。佛罗伦萨人口中有80个注册律师,有600个公证人。另外还有60个医生、外科医生和几百个香料商人。其他的各种商人不计其数,大约有300个佛罗伦萨商人是在外邦经商。佛罗伦萨共有146个面包房⑧。
更为重要的是,意大利的公民力量也很强。并非所有市民都具有公民身份,因为公民身份只给予对城邦中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男性)。以14世纪的佛罗伦萨为例:在9万人口中,有2.5万名男性被赋予了公民资格,可以佩戴武器。其中有1500个贵族和担任公职的权贵,还包括75名骑士。在建立民众政府之前,一共有250名骑士,民众政府建立后,政府官员就不再授予骑士称号,导致骑士人数锐减⑨。公民是指被授予了公民资格(citizenship)的市民,他们被赋予了参与政治的权利。16世纪前,国际贸易、手工业发展和地产的占有更为公民制度发展提供了新的背景。与产业有关的专业人士如律师、法官成为城邦中地位显著的人物,他们的地位,往往要高于小贵族。在一些城邦里,因为拥有富裕的财产和政府公职,公证人也成为市民的上层,加入到了公民的行列。教育程度、专业训练、财富多寡是评价公民等级的主要标准。公民阶层是由律师、政府官员、医生、知识分子(尤指专业化人士)组成的,他们之下是商人、师傅、帮工、学徒和城市无产者⑩。
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为公民参政提供了社会支持。斗争最初是以市民争取选举权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城市的议会往往掌握在权贵家族手里,他们之中有的是旧贵族,有的则是在城市里通过贸易经商而发达起来的新兴阶级。正是这些人,剥夺了城市平民的选举权。斯金纳告诉我们,发难的形式是另行成立平民会议(popolo),为首者是平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领袖——平民议会议长。这是对传统的市政官的挑战,旨在废除市政官的任命必须由显贵家族提名的传统。这样的平民会议很快在意大利兴起,卢卡(1230年)、佛罗伦萨(1230年)、锡耶纳(1262年)都成立了平民会议,并且开展了驱逐贵族的行动。1287年锡耶纳的平民会议在该城从市政官手里夺取了全部控制权,放逐了许多贵族,成立了“九长官委员会”,即一直延续到1355年的商人寡头政体(11)。佛罗伦萨的情况与此类似,1282年佛罗伦萨以平民为基础的“白衣派”设法驱逐了权贵的“黑衣派”,并于1293年进而建立了一种有计划地将贵族排除在执政的行政长官职务之外的体制(12)。1293年,贵族的统治被推翻,建立了行会民主政权,行政机关由六名行政官组成,任期两月,期满改选,代表富裕市民阶级,即羊毛商、丝绸商、呢绒场主、毛皮商、银钱商、律师以及医生和药剂师七大行会,称为“肥人”。民主政府还不准贵族担任行政官。1293年颁布的“正义法规”规定凡没有实际从事一种行业者,一律不得担任公职,严格限制了贵族的政治权利。1295年,对法规进行修订,规定非豪门的贵族,只要加入一种行会,允许担任公职。出身小贵族的但丁,为了参与政治活动,加入了医师和药剂师行会(13)。
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在某些城邦中却导致了城市贵族对城市的控制。斯金纳告诉我们一个维罗纳的例子,在这个城市里,蒙特齐——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与人交恶的蒙太古家族的原型——为平民与根基较深的贵族激烈抗争了二十余载,终于在1226年夺取了对该城的控制(14)。有的时候,即使平民掌握了政权,也有可能遭遇贵族的复辟,例如佛罗伦萨的“白衣派”于1301年遭到了科索·道纳蒂领导的贵族“黑衣派”的直接挑战并被推翻(15)。这导致了世袭家族统治的出现。费拉拉的埃敦家族设法于1264年把对城市的控制权从埃斯特的阿佐传到了其子奥比佐的手里,后者被费拉拉城立为“永久的君主”。同样,维罗纳的通过选举产生的平民会议议长斯卡拉的马斯蒂诺也利用职权建立了一个王朝,他于1277年被谋杀后,其弟阿尔伯托立即被立为维罗纳的领主和终身总督(1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些城邦是共和制,有的城邦是君主制,但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却是共同的特征。与传统意义上的封建贵族不同,城市贵族是些大商人和银行家,其力量还没有大到足以控制一切的程度。银行家的财产来源很复杂,巨额收入来自于土地和矿业的投资,银行和对印度远征的投资。最值得注意的是工商业阶层的兴起。自13世纪起,资产阶级就成为城市权贵集团的中坚力量。资产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是显贵世家,好几代都是意大利的富人,也有部分人士是新兴的中等阶级,如商人、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在他们之下,是一个中产市民阶层,如作坊主、店主。工人和工资阶层也兴起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尽管商人和银行家们兴起并且成为城市的领袖,但他们与民众的矛盾还没有上升到对立的程度。这样,他们与民众就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反映出当时意大利城邦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
在意大利,各个城邦经常受到外敌入侵和城邦间战争的威胁。入侵意大利的外国势力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和他的对手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查理继承了荷兰、西班牙、西西里,以及意大利南部等许多地方的统治权(西西里与南意大利当时属于西班牙的亚拉冈),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后,更通过战争获得了意大利的米兰公国。查理的弟弟斐迪南所继承的领地是奥地利,也用战争和联姻的方法兼并了波希米亚、匈牙利,后来继查理五世之后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与哈布斯堡皇族争霸的是法国的君主们。雄心勃勃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坚持认为米兰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为法国所有,于1494年带兵侵入意大利。哈布斯堡皇族和法国君主之间的战争,使欧洲和意大利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如何结束意大利的分裂、实现政治统一、抵御外敌入侵、维护意大利的自由,是城市贵族和意大利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和最为迫切的政治要求。
简言之,市民力量的强大、公民参政的传统、封建制度的薄弱、市民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新兴资产阶级掌权以及为抵御外强入侵的局势,形成了城市贵族和人民的有限结盟的背景。意大利的城邦规模不大,经常性的战争和城市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民众向政府交纳赋税,也需要知识精英参与政府管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参政迅速发展,成为维持城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文艺复兴创立时期的道德政治论
1300年至1370年这70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创立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深刻影响了公民阶层的社会稳定。一方面,新的发展机会就在眼前:知识精英可以通过训练进入精英圈子。但同时他们又面临着社会变化的另一个结果:执掌权力的是城市中的富裕人士,除了专业知识和社会声望之外,知识精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这种背景导致了公民参与政治的两种方式:要么通过努力直接在政府中担任公职,要么利用自己在律法、文学和修辞上的特长,撰写政治性的论著,通过对统治者的规劝和对人民的宣传,来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人物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都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参与政治的。
在公民的圈子里,知识精英的位置非常奇特。他们处于城市贵族和城市平民的中间,一方面,他们与城市贵族周旋,与同样具有公民身份的惟利是图的行会首领为伍。与城市贵族和行会领袖相比,他们深知自己属于一个以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团体。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城市平民的领袖,深刻感到平民势力的单薄,同时又为城邦内部缺乏凝聚力而担忧。他们敏锐地感到,要想成功地维持城邦的独立,要想有效地抵御外强的入侵,文化落后并且正在分裂的城邦是很难承担此项任务的。他们非常担心,权力争夺、贫富分化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他们富有远见,真诚想为城邦找到一种长治久安的良方,但是这种超前的抱负,却无法为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正如英国学者丹尼斯·哈伊所指出的那样:“14世纪意大利文化史上的三位杰出人物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如何地缺乏基础。”(17)
我们以彼特拉克的感叹来对此印证。在1370年11月29日写给朋友塞里科的信中,彼特拉克表明了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我来说,我们此生所处的是片令我们劳累的硬土,是危机的训练营,是座充满错误的迷宫,是江湖骗子们的军队,是令人惊愕的沙漠,那是一片淤泥堆成的沼泽,一片焦土,一个崎岖不平的村子,一座陡峭山壁,一个黑暗的洞穴,一个群兽纵横的巢穴,一片不毛之地,一块石头地,一块长满了刺的木头,一片毒蛇遍布的草地,一个没有鲜果的花园,一种无止境的忧虑,一条由人的眼泪滴成的河流,一个痛苦之海。”为此,彼特拉克感到“无法安睡”,他的结论是:“生活比这些还要糟糕,还要腐败,我和世人都无法形容。但是,智者如你,从我简单勾画的语言里,可以洞察我的内心。”(18)
上述状况说明,当时精英们敏锐地关注一个问题:如何找到一种让人们正当生活的社会标准,一方面,遏制统治者们对人民的过分剥夺,另一方面,又为民众提供一种躲避灾难的指南。
详细解释善恶体系理论的《神曲》,正是以鲜明的道德对峙为基础的:天堂与地狱、光明与黑暗、美德与陋习、理性与愚昧、善与恶、仁爱与残暴。根据基督教上帝审判的传统,但丁断言人最终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在进入幽冥世界时,地狱之门的门楣上现出这样的文字:“由我进入愁苦之城,由我进入永劫之苦,由我进入万劫不复的人群中。正义推动了崇高的造物主,神圣的力量、最高的智慧、本原的爱创造了我。在我以前未有造物,除了永久存在的以外,而我也将永世长存。进来的人们,你们必须把一切希望抛开!”(19) 但丁在此给出了一个超自然的报应体系,通俗地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道理:神是根据人的行为进行审判的,恶人咎由自取,善人得到神助。一切恶人因为偏离了神定的正道而万劫不复,一切善行则能够得到神的褒奖。因此,只要观察神所判定的结果,就不仅能够看到人类所有行为的后果,还能度量出人与天意(真理)之间的距离。
但丁通过对坏人坏事的一番描述,把各种人类的罪行将按照其轻重加以排列。地狱的外围是一些怯弱无为者,而地狱的第一层住的是一些未曾受洗的婴儿和信奉异教的伟人,如荷马、贺拉斯、奥维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从第二层开始则住着需要受惩罚的罪人,从第二至第六层住着犯有无节制罪的人,包括犯有邪淫、贪食、吝啬、浪费、易怒罪者和信奉异端邪说者。地狱的第七层在一个深渊之下,住的都是犯有暴力罪的鬼魂:对他人施暴者如杀人者、抢劫者;对自己施暴者如自杀者、挥霍无度者;以及罪恶更为严重的对上帝、对自然、对艺术施加暴力者如亵渎神者、鸡奸者和放高利贷者。在第七层和一个悬崖之下是地狱的第八层,共有十个恶囊,仍然按照从轻到重的原则,住着对非信任者犯欺诈罪的人:如淫媒和诱拐者、阿谀奉承者、买卖圣职者、预言者、贪污者、伪善者、偷盗财务者、搞阴谋诡计者、制造分裂不和者和假冒伪造者。在第十个恶囊之下是一个地狱的巨人井,其下是第九层地狱,在其四个恶环里,住着对信任者犯欺诈罪者:即叛卖亲属者、叛卖国家者、叛卖宾客者和叛卖恩人者。在叛卖恩人者之下的就是魔鬼。地狱中鬼魂罪行严重的程度,是严格按照其距离魔鬼的远近来加以确定的。
但丁认为:很多罪行是由贪心引起的。他这么写道:“贪心啊,你使世人沉没到你的水下那样深,以至于谁都没有力量从你的波浪中抬起眼睛!为善的愿望在人们心中当然还会开花;但是连续的阴雨使结成的李子变成虫蛀的李子。”结果,“信仰和纯洁只在儿童中发现;以后,在他们的两颊还没长满胡子以前,这两种美德就都消失了。有些小孩在说话还口齿不清的时期守斋,以后,舌头发音变得流利无阻时,他就不管在什么月,面对什么食物都狼吞虎咽;有些在说话还口齿不清的时期热爱并听从他的母亲,以后,学得能说会道时,就渴望看到她被埋葬。”(20)
但丁认为,正因为贪婪和肉欲如此有效地控制了人们,从青年时起人就倾向于邪恶。人们过着非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不再惧怕上帝,不再考虑兄弟之爱,这样基督教信仰就从人们心中离去。每个人都力求以不名誉的方式胜过别人,这样,假的基督徒就产生了。但丁指出:“你瞧,许多喊‘基督,基督!’的人,在最后审判时,将比不知道基督的人距离他要远得多。”(21) 因此,但丁提倡人必须时刻观察自己的道德品质,因为无论何人产生的善行或恶行,无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在神那里都被计算得一清二楚。所以,人的归宿乃是自己行为所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则,无论是在天国还是尘世,都被认可并被认真加以执行。
在《神曲·天国》篇中,作者的语调变得轻快起来,因为但丁在这里讨论了人如何脱离罪行的方式。按照但丁的说法,人类原本享有一切的天赋,只是罪剥夺了他的自由,使他不再和至善相似。为了让人获得新生,但丁提出了人文主义政治学的一些原则。
首先,但丁认为公民必须履行职责、积极参与城邦事务。在青年时代,但丁曾参加过对吉柏林党作战的康帕迪诺战役。其后,掌握佛罗伦萨政权的归尔夫党因在对待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的态度问题上出现分歧,分裂为支持教皇的黑党和反对教皇贪婪腐败的白党,但丁站在白党一方,结果在1302年黑党取得政权后遭到革职和驱逐。在其后的19年中,被逐出佛罗伦萨的但丁四处流亡,直至1321年在拉文纳逝世。根据布鲁尼撰写的《但丁传》,但丁是一个战士,一个服务于社会的人,一个担任执政官公职的人:他“过着正直、勤学的市民生活。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共和国里服务,最后,当他到达一定年龄时,他成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之一,那时并不是像现在这样靠抽签决定,而是通过投票的方式选出当选人,但丁从此开始了他的执政生涯”(22)。
其次,但丁提出了建立世界帝国的理想。这个政体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必须是统一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方平安。但丁指出:“一个城市的目的是安居乐业,自给自足,那么,不管这个城市的市政是健全还是腐败,这个城市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体。否则,不仅公民生活达不到其目标,城市也就不成为城市了。”他认为,“以一个国家为例,它的目的与城市相同,只是维护和平的责任更重。它必须有一个单一的政府实行统治和执政,否则国家的目的就难以达到。”这是因为,“一个内部互相攻讦的王国必遭毁灭(23)。”除了保卫和平、平息内部纷争之外,国家还拥有如下使命:其一,是实现统一,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也应像上帝那样是个统一体。”其二,是要“把人的贪欲减至最小程度,使正义的威力获得最大发挥”。其三,要求“服从理性,只有全心全意为实现人类的目标而奋斗,人类才有自由”。而“这样的自由,只有在世界政治机构的治理下,才有可能实现”。其四,是实行法制,国家应当“制订引导全人类走向和平的法律,世界政体就能最有效地领导各个地方政体”。最后,这种政体当以“存在”和“善”为其根本,但丁指出:“善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的统一性。既然协调一致本来就是善,那么很显然,协调一致的根源就显而易见了。协调一致是众多意志的一致行动;从这个定义中我们看到,一切行动是由于意志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就是协调一致的根源,甚至是它存在本身。”但丁引用《圣经》的话:“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24)
第三,但丁提出了仁爱和德治的原则。仁爱可以化为各种美德,不仅包括个人品行上的美德如智慧、谦逊、俭约、自制、正直、勇敢、坚韧、坚持正义、不贪婪、不追逐私欲的满足,还包括一种公共的美德,即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及和平、公正、奉献和自由。在但丁那里,这种关系是以仁爱和善心为特征的:他指出,只要善的品质传到人间,世界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善一被人理解是善,就在人心里燃起对它的爱,善越大,人对它的爱也就越大。因此,每个洞察这个论断所根据的真理者的心,都必然爱那至高无上的实体超过它爱其他的事物,因为在这一本体之外的每一种善都只不过是其光辉的一种反射而已。”(25)
第四,但丁提出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他主张政治和宗教分离,主张按照人的美德来区分人类。因为这样,世俗的秩序就必须满足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重要道德原则。平等的原则认为:如果人的行为是以道德而论,那么,教皇、皇帝、国王、贵族和一般的人之间就并无高低之分。
《神曲》完成将近半个多世纪后,彼特拉克的《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就出现了,它后来成为反映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如果说《神曲》是确立了道德治国的基本原则,那么,《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就为道德治国的切实实行提供了精确的指南。事实上,彼特拉克(1304—1374)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发动者。作为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政治思想无疑是现实社会的一种产物。与但丁不同,彼特拉克不再从对神灵的膜拜中来告诫人类防范作恶,他更加关注社会的公益和民生问题。在《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一文中,他提出了政府的职责和政治的准则,这对以后的人文主义政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彼特拉克对于中世纪封建文化的批判是非常彻底的。在但丁那里,人的新生是向天国的靠拢;但对于彼特拉克而言,这种新生只能是通过改革社会制度来加以获得。他倾向于把他自己生活的时代,视为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端。他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法。照他看来,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辉煌的古典时期,《黑暗的中世纪》(从罗马帝国崩溃至他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以及从他开始的文艺复兴新时代。
在《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中,彼特拉克对帕多瓦的君主提出了恳切的忠告:“您必须做你臣民的父亲而不是他们的主人,必须爱他们如你自己的儿女,如你自己的手足。武器、卫士、军队,可用来对付敌人——对于您的臣民,善意就足够了。我所说的人民自然是指那些热爱现存制度的人说的;那些每天都希望变革的人是反叛者和叛徒,对于他们要用严峻的法律加以制裁。”(26)
与《神曲》一样,《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也提倡美德社会,认为唯有实施美德才能获得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但是与《神曲》不同的是,《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更多谈论的不是什么修身养性,而是探讨政治美德的标准,即确立统治者应当如何治理城邦的原则。在一段赞扬统治者法兰西斯科的话里,彼特拉克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政府里的经验和年头已经让您得心应手,您不但被自己的市民们认为是杰出的领主,而且许多其他城市的领主们也有同样的看法。您从不让自己骄奢淫逸,也不享受闲散之乐,您只是兢兢业业的统治,而所有人都认为您平和而不软弱,威严而不傲慢。所以,您的性格既谦逊又宽宏。因而您很有威严。尽管,由于您那异常的仁慈,您让最卑微的人也很容易和您接近,您同时还让女儿们与遥远土地上的贵族家庭缔结了非常有利的婚姻,这乃是您最卓越的作为之一。
您已经成为那些热爱公共秩序与和平的统治者之一,在帕多瓦实行公社政体或者您家族中任何一位成员统治帕多瓦的时候,不论他们掌权多久,市民们从未认为这种和平是可能的——您一个人便在帕多瓦边境的合适之地建筑了许多结实的堡垒。因此,在每个方面您都让市民们感受到您作为统治者的自由和安全,并且,没有人无辜地流血(27)。
从上述段落中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的结论。彼特拉克描述了这样一个理想政府,在这个政府治理下,民众的基本需要如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和平、节俭、财政充裕等都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从形式上说,这仍然是一个由君主掌权的城邦,但人民的意愿必须为政府所吸纳。这是因为,人民的要求正是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础,在这里,统治者的美德是同公众的期望相一致的。简言之,彼特拉克渴望建立一种统治者与民众结盟的政治共同体,其中政府能否体现人民的意愿是政治的关键所在。这种联盟是需要用实践来加以检验的,正如彼特拉克所言:“当事实自己能说话的时候,细枝末叶地赞美就只是一种愉快的练习了。”(28)
在《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彼特拉克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到了首位,视其为政府行政的最重要职责。这里的要素是: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管理;政府需要呈现一定的透明度;民心的向背是关系到政权能否成立的关键。在共同利益的观念下,尽管统治者仍然是大权在握,他却无法在政治上专断独行,而必须要根据民意,把解决民生问题纳入到公共生活的结构中去。由此可见,民众服从于国家、政府保障民众利益,只有这样的互动,才能保障城邦的安宁和秩序。
公共的善,或者是政治的善,涉及到非常具体的民生问题。这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从国家的范围看,政府需要进行各种公共建设,如修缮城墙,处理城市的下水道和处理城市附近的沼泽地带,兴修各种水利工程,清扫街道,办好教育尤其是办好大学,防止狂暴的猪群在街道中乱跑,开凿运河,保障城市的良好的秩序,改进城市的公共设施,不让人们在举行丧礼的时候雇佣妇女们号哭。从关注民众的生活方面看,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统治者要有热爱民众的美德,像爱自己那样去爱自己统治的民众。彼特拉克试图劝说统治者加强与人民的联盟,因为得到人民的爱戴才是赢得城邦安全的根本保证。他以罗马为例,指出恺撒的权力和财富未能保护他不受众人的憎恨,原因在于憎恨是毁灭之源,因此爱就是毁灭的对立面的根本(29)。
值得注意的是,彼特拉克提出了公爱和私爱需要加以区分的理念。仁爱不只是统治者私人品德方面的事情,因为还有着公爱和私爱的区别。私爱是爱自己,公爱是爱大家,关键在于如果如希望被人爱,那就首先需要去爱人。意思是说,领主应当把爱付出,并且不把爱视为一种纯粹的政治游戏。用这样的标准,就可以区分两种统治者,一种是深受国民爱戴的“国家的父亲”,另一种却是国家和信仰的敌人。从理论上来说,公爱在程度上说是要超过私爱的,因为一个父亲很容易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公民的人数要比子女的人数多得多,所以统治者要把公民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要像爱自己身体、灵魂那样来爱城邦里的人民。因为,“一个总是令人愉快的、公正的、乐于助人的、总是以朋友身份出现的人,谁能够不爱他呢?”这种仁爱必定是有回报的,藉此国家的安全得以保证:“优秀的统治者们习惯给予国民们的馈赠,那么,在公民中间,自然就会发展出一笔巨大的善意的储备,他能够为一个持久的政府提供有力客观的基础。”(30)
第二,认为解决穷人的吃饭问题才是真正的美德。彼特拉克引用罗马韦斯帕恩的话,“因为没有人比一个饥肠辘辘的平民更为可怕,因为‘饥饿的平民不知道畏惧’。”所以一个好君主的做法就是尽力减少贫苦的庶民们的饥饿,为他们准备面包。吃饱了食物以后,没人会比罗马人更快乐。彼特拉克认为这种意见也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濒临绝望,常常是因为食物匮乏,而非缺乏美德。因此,每个国家的幸福更多地是由身体而不是精神的健康快乐所组成的。”彼特拉克引用恺撒·奥古斯都的例子说明政府的调节能力。“当谷物短缺时,他常常以极低的价格进行分配,实际上甚至有时免费地送给了接踵而至的罗马人民。一个君主实行这种政策是值得赞美的,因为这种政策的动机是出于对国家真正的爱和获得赞美的渴望,这样人民才会更快乐地承担赋税,更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更乐于忍受艰难困苦。”彼特拉克还指出:“同一位奥古斯都,他用刻薄严峻的答复平息了人们对于酒类匮乏的抱怨,明白无误地表示他提供谷物不是为了求宠于人,而是为了自己臣民的福利与健康。因为他告诉那些犯渴的人,谷物和酒类之间有巨大区别:前者是生活的必需品,后者却有害于生活。”(31) 同样,一个统治者要尽量减少向人民征收不必要的赋税,他指出:“如果一位统治者下令让他的人民负担某种新的赋税,这种赋税如果不是为了公共的需要他永远也不会想要征收,他得让所有人明白,他是在进行必要的努力,而且这是违背他的意愿的。简言之,他应该说服大家,除非因为实际情况迫使他征收赋税,他自己很乐意不去征收它。如果他能把自己的钱投入一部分到新税中,一定有助于他的好名声。”(32)
第三,与民众结盟是获得城邦安全的惟一途径。城邦的安全和统治者的安全紧密相连,而这正是市民和政府结盟的自然结果。不公正的残暴统治激起人民反抗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例如,罗马皇帝尼禄在最危险的时候,得知他的士兵们已经逃离岗位,他的侍卫们也作鸟兽散。而得到人民爱戴的奥古斯都,在其死亡的灵床边却是找不到武装侍卫的,只有友善的国民、朋友和妻子围绕在身边。无道之君丧权辱国,有道之君得到民众真心爱戴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罗马皇帝多米提安(Domitian),他因为无道被人杀死,而元老院也赞同他的死亡,从铭文中消除他的名字,并且用怨恨的谴责和诽谤来玷污他的名声。元老院还颁布法令取消其帝位(33)。从这些正面的和负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倘若统治者成为暴君,他就自行割断了与民众的联盟,这不仅是国家遭到动荡,也使自身血脉谱系中断。
第四,要保持城市的文明和清洁。彼特拉克这么写道:“我要说的是,这座有着如此杰出荣誉的城市——如果您继续旁观而不阻止,而您能轻而易举地办到这一点——正在被狂暴的群猪们变成一个恐怖而丑陋的牧场!任何地方都能听见它们丑陋的哼哼声,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们用猪嘴拱地。污秽的景象,悲惨的嘈杂!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忍受了很久的不幸,那些来到帕多瓦的人对此都目瞪口呆并且感到异常嫌恶。”彼特拉克建议:“让那些养猪的人把它们圈在一个农场里,那些没有农场的人就把他们的猪关在他们的房子里。那些连房子也没有的人,也不能允许他们破坏其他公民的家园和帕多瓦的美丽。这些养猪人也不应该认为,没有法律的阻碍他们便可以把名城帕多瓦变成一个猪舍!”(34) 对有着恶臭的沼泽排干工程,彼特拉克敦促统治者尽早动工。他甚至考虑了动工需要的款项:“我听说公共基金曾经为这类工程拨过款项,那么完成这项任务就不用向公民们新增收任何赋税,也不会减少公共财政支出,或者动用您的私人财产。”(35)
彼特拉克阐发了一种君主与民众结盟、根据民众需要建立政府行政的思想,这对形成人文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对以政府和民众为核心的近代政治民主理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突出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把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存和安全,视为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彼特拉克不主张人间和天国的相似性,也不主张脱离人的民生问题去空论美德。这样,彼特拉克就触及了公共的善这个命题。在共同利益下,统治者和人民各尽其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政治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从彼特拉克那里开始奠定的。
三、文艺复兴发展时期的自由城邦论
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之后,文艺复兴进入了发展期,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公民参政的思想上也表现出了新的特点。从1370年到1450年这80年,常被称为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它给意大利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从萨鲁塔蒂和布鲁尼等人担负起建立自由城邦的使命中,可以看到它不同于前一时期的进步性。从萨鲁塔蒂和布鲁尼开始,文艺复兴就不再是个人的、文化的运动,它发展成为目标清晰的建立自由城邦的运动。之所以出现这种形势,与萨鲁塔蒂、布鲁尼等人相继在佛罗伦萨担任重要的宣传官职,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一,萨鲁塔蒂、布鲁尼等人致力于社会改革,把参与公共活动、担任社会公职、弘扬共和制度、用文化培养人民的爱国之心,视为文艺复兴运动最为重要的使命。发展时期的知识精英,把早期知识精英极端孤立的个人奋斗转变成个人和社会的契合,提倡个人为社会作出贡献。但丁信奉的与神契合,到了布鲁尼那里,就成了与社会的契合。同样,个人的美德,也为公共的美德所取代。公共的善,因此成为民众为自由城邦服务的基本追求。如同彼特拉克把爱分为私爱和公爱一样,布鲁尼也把犯罪分为私罪和公罪两种:个人犯罪,做错事是出于自己的动机,叫做私罪;公共犯罪,则是出于整个城市的意志。他指出:“犯罪分为公共的和个人的两种,这两者之间区别很大。个人犯罪源出做错事的人自己的动机;而公共犯罪则是因为整个城市的意志。后者不仅仅是听从这个人或是那个人想法的问题,而是城市的法律和传统将什么奉为圭臬的问题了。通常情况下,一个城市会遵从大多数公民的好恶。在其他城市里,大多数公民的意见经常压倒了一小部分好公民;而在佛罗伦萨,大多数公民的意见恰好是同城中最优秀公民的观点相一致的(36)。“布鲁尼的公罪意识论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凡制度不好的地方就会有人犯公罪,与其说犯罪是起因于人的道德低下,毋宁说要归咎于制度上的不完善。与创立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同,布鲁尼习惯于通过完善政府的制度、法律和规则来制止犯罪。他认为公罪要比私罪更加有害。用什么来抵抗这种威胁呢?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公民的共和政治。
第二,发展时期的公民参政思想,明显打上了捍卫共和政治、捍卫自由城邦的烙印。开创时期的知识精英受时代的局限,既没有视共和制度为公民参政最为重要的目标,也没有把政治体制当作为民众谋取利益的最为重要的工具。但丁的国家是由一位贤明的君主统治的。但丁以为,此人必须来自罗马,但却不是教皇。其理由是:罗马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但丁接着指出美德的重要性:“人们一致公认,人是因为具备美德才显得高贵”(37),因此只有贤哲才能够当此权柄。这种把希望寄托于一位贤明的君主的想法,仍然是中世纪君主蒙神召选的传统,所要求的不过是君主应当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管理世界。在但丁和彼特拉克的心目里,罗马时代的恺撒就是这样的一位明君。然而,在布鲁尼那里,佛罗伦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的共和时代,而恺撒,则是一个摧毁共和体制的暴君。布鲁尼指出:(佛罗伦萨)这座高贵的城市建成的时候,也就是罗马人的统治极度繁盛的时候,是强大的国王和好战的民族纷纷被罗马人的武力和美德征服的时候。当时,迦太基、西班牙、科林斯都被铲平,八方土地、四海波涛,无不归于罗马人的统治,而罗马人则从不曾遭受外国的侵害。也就在那个时候,人民的自由尚不曾被恺撒、安东尼、提比略、尼禄这些毒害和毁灭了罗马共和国的人所剥夺。相反,神圣而未被践踏的自由仍在成长之中。而在佛罗伦萨建成不久,却被那些最邪恶的盗贼窃去了。出于这个原因,我想有些东西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会比其他城市更为真实,过去是,现在也是:那就是,佛罗伦萨人享有格外完美的自由,他们是暴君最大的敌人(38)。结论是:“所以我相信,从佛罗伦萨建城之日起,对于罗马的毁灭者,对于共和国的破坏者,这座城市就怀有深切的仇恨,直到今日也不曾遗忘。如果那些堕落者的蛛丝马迹甚至只是名字保留到了现在,他们会在佛罗伦萨受到痛恨和诅咒。”(39)
这种捍卫城邦的独立和自由的人文主义政治观不但和但丁的道德论不同,就是和彼特拉克、薄伽丘那种批判中世纪传统、关注民生的美德观也不一样。它旨在建立自由城邦和公民社会,乐观地认为只要民众团结一致,建立公民的共和国是可能的。它强调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要求人民为捍卫这种自由、保卫共同利益而献身。既然个人的尊严全靠社会良好的制度来实现,因此公民也必须为城邦服务。在公共利益的旗帜下,实现自由城邦的目标就有赖于建立起政府和民众的互相支持和互相合作。
第三,这种信仰的结果就是,通过对古代罗马政治和邻国政治的比较,确立建立公民共和国的制度。布鲁尼这样发出感叹:“对于佛罗伦萨人来说,对共和制度的情感并不是新鲜事,也不是一时兴起(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相反,从某些罪大恶极的人摧毁了罗马人的自由、光荣和尊严的时候起,他们对暴君的斗争就开始了。那时,佛罗伦萨人的心中燃烧着对自由的渴望,开始积蓄起对共和国的热情和为此斗争的信念,直至今日。……这种态度的起因与其说是为了维护祖先国土应受的尊严,不如说是出于对暴君的正义仇恨。”(40) 布鲁尼历数邪恶暴君的罪行,如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用一把剑横扫元老院,它杀死了最杰出的执政官,他每天都要像宰杀牲畜那样屠戮城中能看到的任何平民”(41);如提比略·恺撒,“我们还曾听闻过什么比他折磨和灭绝卡普里岛上的罗马公民更无耻、更令人唾弃的暴行吗?还有什么比这位皇帝的情人和男宠以及他们邪恶的性行为更令意大利蒙羞的吗?——如此堕落的人居然曾经生活在这里?”(42) 正因为有如此的历史教训,所以佛罗伦萨人就选择了抵御暴君的共和制度。因为佛罗伦萨人“不允许自己被怠惰和怯懦玷污,也不满足于躺在先辈的光荣上晒太阳,或是枕着荣誉悠闲地享受”。相反,“佛罗伦萨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并且获得威望和荣誉”(43)。
接下来是对佛罗伦萨优秀行为的一番简述,主要包括发展工商业、帮助弱者和资助被其他城邦流放的人、在邻国遭受侵犯时加以慷慨援助、守信和对盟友忠诚、勇敢地抵抗侵略等等。如果说这些光辉成就证明了佛罗伦萨是整个意大利最具有美德的城邦的话,那么,它的基础就是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例如:政府官员的设立是为了实施公正原则、官员是公民的管理者而不是专制统治者,为此政府做出许多规定,保证他们不会高高在上,或者动摇佛罗伦萨伟大自由的基石。代表国家主权的最高首脑不是一人而是九人,任期仅两个月,以便抑制长官可能产生的优越感。城市分为四个区,每区选出两人,保证各区都有自己的代表。首席执政则是从四个区轮流选出的,必须是道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它的称号就是正义旗手。此外,执政团不是单独行动的,它和十二贤人团(九位最高长官的顾问,协商政务)、旗手团(维护自由的武装力量,参加顾问会议)一起协商,在重大的问题上,还要由人民大会(Council of the People)和公社大会(Council of the Commune)做最后裁决。因为“佛罗伦萨人认为,涉及大多数人的事务,应该由全体公民按照法律程序做出决定。这样,在这座神圣的城市里,自由得到了发展,公正得到了保障。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没有谁可以凭借一己臆想而否定大多数人的决策”(44)。
当然,我们无法确知知识精英为佛罗伦萨设计的这些政治制度到底有多么深刻并究竟能够给人民带来多少的自由和民主。不过,有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自由城邦的理论可以吸引民众。在知识精英的号召下,民主、平等和公正被提了出来,以往处于一盘散沙的平民被团结了起来,在公民阶层的领导下,成为抵御专制的重要力量。这个处方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一个佛罗伦萨人必须遵循共和、民主和自由的美德,这种美德既然与一个由城市显贵、公民、平民组成的社会息息相关,那么,在共同利益的旗帜下,就有可能缓和城邦内部的矛盾,而这正是城邦繁荣、有力抵御外强的最有力保证。正如佛罗伦萨史专家鲁宾斯坦教授(Nicolai Rubinstein)对于当时佛罗伦萨自由概念的分析,结论是“这种自由包括从政治独立到共和国自治等等概念。对佛罗伦萨和托斯卡那地区其他的自由共和国来讲,这二者是相互交织着的。因为这里的政治豁免权同城市自治政府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对尘世间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独立和主权‘更珍贵和更令人高兴’。这是人们期望的东西……这也就是祖国的自由。”(45)
四、文艺复兴晚期的君主论
1450年至1530年这80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晚期,政治上的特征就是君主制度在意大利和欧洲确立。在这个时期,阶级关系是十分紧张的,由于力量对比的关系,意大利各个城邦最后都由大的显贵家族掌握了政权。以佛罗伦萨为例,15世纪末期产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美第奇家族的权势渗透到佛罗伦萨的每一个角落,市民的怨恨积蓄已久,终于爆发了1494年把美第奇家族驱逐出佛罗伦萨的事件。但是,佛罗伦萨政府并不能恢复对城邦的有效控制,于是美第奇家族借用外国力量于1512年复辟,继续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混乱的局面始终不能了结,更因为美第奇家族是依靠教皇和外国势力复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自由变得岌岌可危。1532年美第奇家族成员成为公爵,佛罗伦萨也从一个共和国转变成了实行君主制度的公爵领。
这一阶段的公民参政是在君主制度已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产生的。马基雅维里、圭恰迪尼和巴尔德萨·卡斯蒂格利奥(Baldesar Castigilione)的著作,是反映这一时期公民参政思想的代表作。因为君主制度在当时已是意大利和欧洲各国的主要政治制度,因此必须对此进行重点研究。
君主制度下的公民参政思想有什么主要特征呢?我们把它与前两种思想做一个比较。在创立时期的公民参政,主要考虑的是建立社会道德秩序,要求建立起一定的社会规范,来使民众的基本权益得以保障。公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参与政治,或者通过劝说统治者,来建立这种道德规范。在发展时期,因为民众已经团结起来,知识精英又在一定的范畴内掌握了权力,因此,就以自由城邦为号召,要求完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建立人民的自由共和国。在文艺复兴晚期的君主制时代,意大利各个城邦已经由像美第奇家族那样的城市显贵掌权,公民参政的思想就越来越反映在如何奠定近代政治学的规则上。当然,这一时期的公民参政思想仍然保留着维护民权这一与前两个时代相同的基本特征。然而,在公民参政思想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殊内容,反映出这一特定时期政治思想上的新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对大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认识:民众和城市显贵之间的结盟关系已经破裂;公民社会已经不复存在,转变为君主统治下的臣民社会;政府已经转变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专政;选举制度已经为官僚任命制度所取代;城邦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已不复存在,大资产阶级已经走向专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德统治和贤人政治成了一句空话,作为道德哲学和公民自由的一种替代品,专门论述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则的近代政治学诞生了。
这就出现了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对城市显贵政权(新君主)性质的深刻揭示。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不再谈民众应当如何与君主结盟的问题,但却深刻剖析君主政府的实质及其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对立。他明确指出:自由是需要暴力来加以维护的。在他所有的分析中,以仁义为调和手段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合作不见了,有的只是一种透彻的利害关系:如果统治者过分压迫人民,必定会危及统治者自己。马基雅维里视君主制为人民自由的对立面,君主与人民的关系只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他希望人们认清楚大资产阶级(新君主)的这个本质,不要再对这样的城市贵族政府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同样,维护人民的权益,也就成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这个主题在《君主论》中反复被陈述。马基雅维里这么说:“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民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46) 他又说:“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47) 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里在陈述人民利益必须得到保障时,也改变了论证的方式。他不再赋予君主更多的道德责任,而是通过利害关系的陈述,提出了过分剥削人民必将给统治者自己带来祸害的论点。即便是最愿意剥削民众的君主现在也能履行对于民众一定的责任了——或者这正是马基雅维里想要让那些阅读他著作的统治者相信的。
于是,马基雅维里对君主政府的看法暗示着一个新的原则:政治秩序的建立或运行不再与君主个人的道德行为相联系,因为后者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或根据利害原则来确立政策。诚然,在城市显贵还在同民众结盟的时候,道德的运作是有效的:只要人人都在行善事,或者在行善事时都有足够的努力和耐心,几乎所有的人就都会从中得到益处。但是,当君主对人民背信弃义时,尽管内心深处还是盼望统治者能够根据善心行事,但这在逻辑上已经不再成立,因为此时的君主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因此也就没有了能够对任何社会阶层都有利益可言的道德约束。马基雅维里在重申现存政治结构只偏重统治者利益的同时,证明在结盟时期的所谓统治者的美德如慷慨、仁慈、守信等,到头来只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并且无助于国家的巩固。例如:“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奢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得到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48) 马基雅维里声称,“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穷困以至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致变成勒索之徒,君主对于招来吝啬之名不应该有所介意。”(49)
大显贵家族直接掌权的形势决定了政权的反人民性增强,然而,在当时外敌入侵、佛罗伦萨随时都有可能丧失独立的情况下,这一形势又促使了马基雅维里与大显贵家族的暂时联合。问题只是如何保证佛罗伦萨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为了这一目的,马基雅维里担任政府公职。从1498年任第二秘书厅的长官起到1512年被免除一切公职,共有14年,相当于从他的28岁一直服务到他的43岁,正是他的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当时佛罗伦萨的首席执政官是皮埃罗·索德里尼,马基雅维里得到重用。在这段时期内他干了几件事情,全是为了佛罗伦萨的强大和安全服务的。他的主要任务,既然是维护城邦的安全,因此他就致力于外交斡旋和筹建一支佛罗伦萨的国民军。作为外教特使,他出访过罗马(1503年)、瑞士和法国(1507年)。1507年的使命是艰巨的,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准备从法国进攻意大利,他的使命就是想去通过外交斡旋,阻止这种对于意大利的侵犯。为了有效保卫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一直致力于建立佛罗伦萨的国民军。这是从本国的居民中招募的,用以取代飞扬跋扈、纪律松弛、没有爱国心的雇佣军。同样的使命也表现在1510年的出访法国,期望法王路易十二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解,目的也是阻止外敌侵犯佛罗伦萨。1511年教皇的军队讨伐佛罗伦萨,罢黜了索德里尼,次年,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成为城邦的主人,马基雅维里被解除一切职务。美第奇家族又指控马基雅维里参与反对自己的统治阴谋,因此在1513年把他投入监狱,后经马基雅维里的辩解获释。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和《君主论》,就是在出狱后不久问世的。马基雅维里把《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洛伦佐,但后者却并没有启用马基雅维里。直到洛伦佐死后,马基雅维里才在枢机主教朱理·美第奇管辖佛罗伦萨时期承担起一定的外交事务,并被选为共和国的史官。1525年马基雅维里完成名著《佛罗伦萨史》,1526年当选为城防委员会的秘书。马基雅维里于1527年逝世,他生命最后的十几年,是在探寻政治学、历史学奥秘的思索过程中度过的。从这些情况看,马基雅维里是一个对时局有深刻认识的、精通外交的政治家,他关心共和国的安全,乃是很自然的事(50)。
另一方面,马基雅维里也通过著作告诉统治者究竟什么才是治国之道。在国难当头、人民受苦的形势下,马基雅维里甚至更加努力地去寻找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方法。他指责各种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甚至对人性向善这个基本原则进行否定。但更为重要的是,马基雅维里阐明了国家的基本宗旨在于自己强大,这样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此,他不仅分析各种君主国的优势和弱势,而且还着重论述了军队、用人、君主之为人,以及最后“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正如英国学者约翰·麦克里兰(J. S. McClelland)所说:“马基雅维里的君主,其国家全无封建痕迹,君主与人民之间没有中介建制。”(51) 如上所述,尽管马基雅维里揭示出显贵家族统治的反人民本质,但是在民族矛盾居主要地位的时候,他的强国、卫国方略,在当时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里这位对君主制度研究进行过最为透彻分析的政治思想家,却是最完善的公民社会的提倡者。J. G. A. 波考克作《马基雅维里式的关键时刻》,有过解释。该书2003年新版书跋云:“我发现斯金纳对‘西塞罗式’公民概念与我和巴伦在最终意义上提出的‘马基雅维里式’公民概念相对立,它旨在将共和国重建为法与正义之下的公民共同体,而不是关注某一有着超强(且具有扩张性的)德性的公民能否通过确立一种平等规则(应当注意的是,它是一种统治的平等,而非权利的平等)实现自我约束。”(52) 该文又指出:“斯金纳所发现的13世纪‘西塞罗式’的公民理想与如下主张是一致的,即公民德性可以在法制和某一公正君主之下付诸实践,因此,生活在奥古斯都、图拉真以及优士丁尼统治下的民众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可以诉诸法律。另一方面,200年后,汉斯·巴伦笔下的佛罗伦萨人仍然有理由坚持认为,在恺撒的统治下,自由荡然无存,结果,君主变成了暴君和魔王,而公民不再具有那种在反对蛮族过程中获得的作为帝国根基的美德。”(53) 我们不能在这里对“西塞罗式”和“马基雅维里式”的公民概念做出更多的分析,只想根据我们这里的研究提出两点:第一,在马基雅维里时代,城市显贵(新君主)与人民的结盟已经破裂,因此不可能在新君主的统治的条件下,建立所谓的自由公民社会;第二,“马基雅维里式”的公民社会,乃是一种没有君主统治的公民共同体。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在公民社会与君主政治之间划出一道严格的界限,认为在新君主制的统治下,只能产生君主和臣民的关系,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则有赖于真正的公民共和国出现,只有在那时,正义、法制才能与民众的公共利益相互吻合,从而体现出了政治制度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
五、结论
过去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思想的人,多着眼于这些思想和建立在法律和正义之下的公民共同体的关系,或偏重于古罗马共和时代的体制和西塞罗的思想对它们的影响。这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但制度本身的改变,或一种新制度的出现,是“决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决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的”(54)。把公民参政的思想和实践联系到当日佛罗伦萨总的政治社会状况来考察,就不能不注意到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及同邻国和外强之间关系紧张的加剧,掌握大权的美第奇家族越来越需要直接占有更多的政治、社会资源,越来越需要有更多的人民为它提供经济资源。就当时公民政治和城市显贵家族的关系来看,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斗争的一面,这一面在当时就表现在知识精英要求建立以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理念不符合城市贵族对社会资源直接占有的要求。就当时的阶级关系看,城市显贵已经无法容忍佛罗伦萨对美第奇家族的驱逐,而知识精英也不得不用犀利的批判暴君的文章来改善自己沦落为朝臣、臣民的悲惨命运。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是不能使大资产阶级顺利地取得对于政治、社会、经济资源全面掌握控制权的。于是,美第奇家族不惜同外部势力勾结,以外部势力和城市显贵家族为靠山,开始在佛罗伦萨实施专制统治——1532年变佛罗伦萨共和国为君主制的公爵领,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资产阶级发动的限制公民参政的重要行动。
意大利公民参政在背景上的特点,是封建关系薄弱、资产阶级掌权和悠久的公民参政传统。这种背景使公民参政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知识精英要求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民共和国。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们不再是统治者控制下的臣民,而是自由城邦的公民,他们自己参政、议政,通过公民选举和公民大会,使政府成为代表民意、执行民意的工具。但是,共和国政府既不拥有自己的军队,也不掌握城邦的经济、政治大权,从而使自己在与城市显贵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尽管这样,所有的公民参政思想如“公共利益”、“自由城邦”、“人民共和国”和“消灭暴君”等,都意味着知识精英们企图调整社会的政治结构。这既是政治道德的发展,也是文艺复兴运动进程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经过了一系列的转变,每一个这样的转变,都使道德和政治成份提高了一步。我们所研究的公民参政思想变化反映了这种政治上的特点。
本文分析了公民参政思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三种类型。文艺复兴运动初期,但丁、彼特拉克透过对当时社会政治和民生的观察,推导出了“美德和德治”的学理框架,其基本内容是让国家体现出爱护人民的道德宗旨。基于国家道德基础的概念,但丁认为,政治的腐败起源于道德的腐败,只要统治者按照道德规范行事,不过分肆意妄为,就能进行道德的统治。与这种理论紧密配合的是天命论,受到时代局限,但丁把非道德的行为归结为统治者背离了神的意愿。彼特拉克在非常不同的领域里界定了道德的观念,他把美德归结于解决民生问题,把腐败归咎于统治者的荒谬和人民固有权利的被侵犯。
1400年后,布鲁尼提出了建立公民共同体的设想。在《佛罗伦萨颂》等纲领中,“自由”和“公共利益”是依靠共和国政府的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公民们的斗争方式已不再是向统治者请愿,而是宣告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在自由城邦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下,人民意愿和共和国政府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即如后来孟德斯鸠所归纳的:“在共和体制下,美德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它就是对共和的热爱。”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共和在民主制度下就是热爱民主”(55)。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由此成为国家和人民之间合作的基础,既是代表民意和道德之善的基础,又是政府政治秩序努力的目标。尽管这一闪耀着人民国家原则光辉的思想未能在意大利长久持续,但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却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但是,从15世纪后期起,随着专制主义和君主制度在意大利出现,公民共和国的理念被极大地削弱。除非废除专制的君主统治,否则公民共和体的政治就不能实现。此时,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加剧,马基雅维里等人,一方面,力图捍卫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提出了“马基雅维里式”的公民概念,宣告了专制君主制和公民共同体在学理上的分野,因为此时新君主统治的政府性质已经发生改变,而不复存在的公民共和体,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政治,即近代政治体制的真正出现。
我们的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思想的变化,反映出运动创立期、发展期和晚期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道德论、自由论和君主论,正好是对应了城邦中人民和城市显贵结盟的三个类型:在运动的开创期,封建贵族尚未被击败,同时资产阶级的羽翼也未丰满,因此出现了民众与资产阶级结盟的局面;至运动的发展期,一方面,存在着众多显贵家族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人民的力量已经强大,这导致了人民和城市显贵结盟关系的发展,出现了自由城邦论和公民共和国这样的观念。到了运动的晚期,城市显贵们已经完全垄断了政权,不仅走向专制、保守,而且限制、压迫人民的阶级本性也逐渐显露。这表明,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君主(如英国和法国的君主)会走向专制,就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城市显贵,也会随着自己地位的稳固,随着对社会全部资源直接控制的需要和对人民共和运动的恐惧,最后也会走向专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瓦解原因,因此不能仅从外敌入侵来加以解释,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掌权的大资产阶级与民众联盟关系的破裂,是大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暴露,这些,才是佛罗伦萨从共和制转变成为君主制度的最根本的原因。
最后,必须指出公民参政思想对近代政治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以往,人们习惯于把自上而下的王权发展道路视为消除封建割据、建立民族国家的主要力量。但是,不仅英国、法国的君主们最后都走上了专制的道路,就是有着大资产阶级出身背景的意大利城市显贵,最后也走上了专制君主的道路。这说明白上而下的由王权发展来建立近代国家的理论是有局限的。从根本上看,近代政治意味着政治程序的民主化、公正化和法制化,因此,还必须依靠自下而上的推动,即公民的参与政治,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这里所分析的三个时期公民参政思想类型差别较大,但都具有人民参政、按照民意来建立近代国家的进步内容。从这些看,文艺复兴并不仅仅是场文化艺术运动,它更是一场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建立近代国家的政治运动。在旧秩序中无法生存的广大人民希望用公民参政的方式克服政治秩序的危机,使它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是公民参政的主要目标。
注释:
① 转引自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绪论第3页。
②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
③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56页。
④ J. G. A. 波考克:《从佛罗伦萨到费城——一部共和国与替代方案之间的辩证史》,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页。
⑤ 例如,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在分析马基雅维里时,就曾正确地强调:马基雅维里注重的是从政治实践中得来的现实经验,古代的例子的作用只是为其理论增加权威性而已。参见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和圭洽迪尼:16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学和历史学》(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53—202页。
⑥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6页。
⑦ 劳罗·马丁尼:《权力和想象: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国家》(Lauro Martines, Power and Imagination, 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朗顿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页。
⑧ 基奥凡尼·维拉尼:《一位公民是如何看待他的城市的》,迪沃多·K.拉布主编:《现代西方的起源:关于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欧洲历史的论文和史料》(Giovanni Villani,“How one Citizen Regard His City,”in Thwodore K. Rabb, Ed., Origins of the Modern West Essays and Sources in Renaissance & Early Modern European History),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1993年纽约版,第179—181页。
⑨ 基奥凡尼·维拉尼:《一位公民是如何看待他的城市的》,迪沃多·K.拉布主编:《现代西方的起源:关于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欧洲历史的论文和史料》,第179—180页。
⑩ 保罗·F.格伦德勒主编:《文艺复兴百科全书》(Paul F. Grendler, ed., Encyclopedia of the Renaissance)第6卷,查理·斯克瑞布尼之子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6页。
(11)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0页。
(12)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第50页。
(13) 田德望译:《译本序——但丁和他的〈神曲〉》,但丁:《神曲·地狱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4)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第51页。
(15)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第51页。
(16)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第51页。
(17) 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4页。
(18) 彼特拉克:《1370年11月29日致罗巴多·达·塞里科的信》(Francis Petrarch:“To Lombardo da Serico”),彼特拉克:《晚年时期的书信》(Letters of Old Age),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页。
(19) 但丁:《神曲·地狱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20) 但丁:《神曲·天国篇》,第167页。
(21) 但丁:《神曲·天国篇》,第122页。
(22) 布鲁尼:《但丁传》(Lionardo Bruni Aretino, The Life of Dante),弗里德里克·乌加出版社1963年版,第84—85页。
(23) 但丁:《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24) 但丁:《论世界帝国》,第23页。
(25) 但丁:《神曲·天国篇》,第158页。
(26) 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
(27) 彼特拉克:《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Francesco Petrarch, “How a Ruler Ought to Govern His State”),本杰明·G. 科尔、罗纳德·G. 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Benjamin G. Kohl and Ronald G. Witt, eds., The Earthly Republic Italian, Humanists 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8—39页。
(28) 彼特拉克:《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38—39页。
(29) 彼特拉克:《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43—44页。
(30) 彼特拉克:《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45—46页。
(31) 彼特拉克:《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56—57页。
(32) 彼特拉克:《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58页。
(33) 彼特拉克:《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47页。
(34) 彼特拉克:《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52页。
(35) 彼特拉克:《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54—55页。
(36) 布鲁尼:《佛罗伦萨颂》(Leonardo Bruni, “Panegyric to the City of Florence”),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37) 但丁:《论世界帝国》,第29页。
(38) 布鲁尼:《佛罗伦萨颂》,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151页。
(39) 布鲁尼:《佛罗伦萨颂》,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151页。
(40) 布鲁尼:《佛罗伦萨颂》,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151—152页。
(41) 布鲁尼:《佛罗伦萨颂》,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151—152页。
(42) 布鲁尼:《佛罗伦萨颂》,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151—152页。
(43) 布鲁尼:《佛罗伦萨颂》,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153页。
(44) 布鲁尼:《佛罗伦萨颂》,本杰明·G.科尔、罗纳德·G.维特主编:《意大利的人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论政府和社会》,第170页。
(45) 转引自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0页。
(46)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页。
(47)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23页。
(48)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6页。
(49)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7页。
(50) 参见惠泉译:《作者小传》,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51)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52) J. G. A. 波考克:《从佛罗伦萨到费城——一部共和国与替代方案之间的辩证史》,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53) J. G. A. 波考克:《从佛罗伦萨到费城——一部共和国与替代方案之间的辩证史》,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第11页。
(54) 参见程应镠:《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55) 转引自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8年6期第92~110页
责任编辑:刘悦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下一篇:古巴比伦时期房产买卖活动论析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