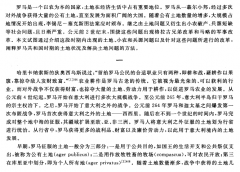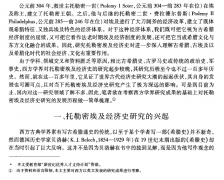论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
【英文标题】Brockton's Notion of Kingship
【作者简介】于洪,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24)
【内容提要】 在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王权变迁的基础上,布拉克顿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法律之下”的传统和基督教“王权神授”的观念,形成了独特的王权观念。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主要包括王权的合法性、国王的权能以及王权的有限性等三个方面。经过科克等人的重新阐释,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王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旗帜,从而成为英国近代宪政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关 键 词】英国/布拉克顿/王权观念
布拉克顿(Henry De Bracton,约1216—1268年)是13世纪英国法学家,德文郡人。他最初是大法官威廉·雷利(William Raleigh)的助手,1245年担任亨利三世巡回法庭的法官,从1248年到1257年成为王座法庭的法官。同时,他还是一位神职人员,从1259年起,相继担任了数个重要的教职,并一度担任埃克塞特大教堂的大法官①。这样的经历使其掌握了习惯法和普通法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还精通教会法和罗马法,这使他能够率先对英国的法律制度进行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所著的《论英国法律与习惯》被梅特兰誉为“英国中世纪法学的王冠和鲜花”②。这部著作由乔治·E. 伍德拜因编纂,以《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为书名出版,成为研究布拉克顿王权观念的重要文献。
长期担任重要司法职务的布拉克顿在其著作中不仅分析了大量的普通法案例,而且还表达了比较系统的王权观念。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集中体现在“国王在任何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The king must not be under man but under God and under the law)”③ 的著名论断中。国内外学者在论述英国王权时大都提及布拉克顿的这一论断,但迄今尚未见到专题研究布拉克顿王权观念的论著,更未曾对布拉克顿王权观念的产生原因、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④。本文欲在解读布拉克顿著作的基础上,结合英国王权的历史变迁,探讨布拉克顿王权观念的产生、内容及其历史影响。
一
布拉克顿王权观念产生的历史基础是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王权发展的实际进程。哈罗德国王在黑斯廷斯战役当中战死之后,威廉就要求约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为其举行加冕典礼,并迫使教俗贵族向其宣誓效忠。在加冕誓言中,威廉保证维护教会的权利,并且持守良法以成为贤明之王⑤。通过加冕典礼,威廉从一个外来的军事征服者成为受上帝恩赐的合法国王。加冕之后,威廉放逐了那些抵抗其征服的贵族,占有了大量地产,并将地产分封给随其征战有功的诺曼人,剥夺了修道院和主教区以及城市固有的自由和特权。威廉还下令禁止民众聚会以防止发生叛乱,后来又对全国的人口和土地进行清查,形成了《末日审判书》⑥。英国的封建制度由此确立,所有封臣都对国王有效忠义务,从而形成了英国独特的封建原则,即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⑦。征服者的王权具有神圣的合法性和现实的权威性,这成为王权实现对王国有效统治的根本。
尽管在威廉治下王权渐趋稳固,但在1075年还是爆发了封建贵族武装反抗国王过分集权的叛乱。这类叛乱在此后一个世纪屡有发生。亨利二世时期由于推行司法改革侵夺了贵族的司法权,也激起了贵族的武装叛乱⑧。显然,贵族成为国王集权的最大障碍,他们在强势王权之下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尽力抵制王权的膨胀。一旦王权处于弱势,贵族则积极主张自己的权益,甚至以武力迫使国王签署限制王权的法律。
斯蒂芬在加冕之时为获得教俗贵族的支持,被迫赋予他们诸多的权利和自由⑨。及至约翰王时期,由于长期对法国用兵,贵族的军役负担加重。约翰王数次兵败大陆,并遭到教皇的巨额勒索,这激起了贵族的强烈反抗⑩。1215年,贵族强迫约翰王签署了《大宪章》,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第十四条,规定国王无权擅自征税,并规定了大会议的召集办法;第六十一条确立了“国王应受监督”和“民众有权合法地反抗国王”的原则(11)。这使得限制国王的征税权合法化,并且为议会的产生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民众反抗国王的暴政确立了法理前提。《大宪章》不只是封建性的,还是授予王国内全部自由人的(12)。1258年,贵族又迫使亨利三世签署了《牛津条例》,这是贵族武装反抗王权的结果,旨在防止亨利三世破坏《大宪章》(13)。《牛津条例》进一步巩固了《大宪章》限制王权的原则。
从《大宪章》到《牛津条例》,王权逐渐受制于封建贵族,实质上是贵族依靠武力优势将王权置于法律约束之下。约翰王与亨利三世都试图打破这一束缚,却在贵族的抵制之下被迫数次重新确认《大宪章》。国王失去了独立的征税权,再加上封建军役的衰落(14),王权可支配的财力和武力都受到了贵族的限制。这些限制在议会出现之后更为巩固,议会是在亨利三世时期由贵族组成的大会议发展而来,并逐渐成为贵族和平民限制王权的常设机构(15)。《大宪章》和《牛津条例》使得王国的统治在更大程度上由贵族掌握。尽管这一时期英国王权在城市市民阶层的支持下有所加强(16),然而市民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远不足以与教俗贵族相抗衡。贵族仍占有大量地产,掌握了主要的社会财富。教俗贵族为维护自身的特权和利益,依靠其现实力量和传统的法律习惯谋求限制王权。国王的集权和教俗贵族对王权的制衡相伴而行,这推动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有限王权(limited monarchy)的形成,孕育了近代宪政的根基。诺曼征服之前的“国王在法律之下”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重生,布拉克顿主张国王要在法律之下,这不仅反映了13世纪英国王权发展的实际状况,而且还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法律之下”的政治传统。
布拉克顿王权观念的思想渊源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和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的核心是“国王在法律之下”:教俗贵族和民众对既有习惯和法律有着普遍的认同,法律先于王权而存在,国王不得轻易变更法律。每一位撒克逊国王在教俗贵族建议之下订立新法之时,首先必须重新确认既有的法律(17)。诺曼征服之后的国王继承了这一传统,威廉一世在入主英国时宣誓,他将持守王国先前存在的法律,尤其是忏悔者爱德华时期的习惯和法律。从亨利一世至亨利三世每位国王都作了同样的宣誓(18),以使其王权获得合法性。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布拉克顿反复强调法律使国王成其为国王,无法律之处则无国王(19)。
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受到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著作的影响(20)。约翰在《论政府原理》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其王权神授观念,约翰认为国王是受上帝派遣来统治地上的万民的,王权源于神权。贤明的国王依法而治,否则就成为暴君,暴君则是以武力压迫民众。然而,约翰主张暴君是受上帝派遣来惩罚邪恶的民众的,暴君的暴政像贤明国王的仁政一样亦是合法的,而且主张只有上帝可以惩罚暴君(21)。显然,约翰以是否依法而治区分了贤明的国王和暴君,但没有否定暴君统治的合法性。实际上,“服从于作为上帝代理人的国王成为信仰的义务,这一点贯穿于整个中世纪”(22)。布拉克顿继承了约翰的王权神授观念,多次强调“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the king is God's vicar)”(23),国王必须在上帝之下。
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王权的变迁是布拉克顿王权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基础;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法律之下”的传统和基督教王权神授的观念是布拉克顿王权观念产生的思想渊源。约翰王和亨利三世时期王权的衰弱,直接为布拉克顿形成以“国王在任何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为核心的王权观念提供了现实条件。布拉克顿长期担任重要的司法职务和教会职务,这使其对王权与贵族的力量消长乃至整个封建等级结构具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王权观念。
二
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主要包括王权的合法性、国王的权能以及王权的有限性等三个方面。王权的合法性是指王权得以产生和存续的基础,即王权能够得到臣民的认同,以使其统治具有权威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国王的权能是指国王所拥有的立法权、司法权等。王权的有限性是指王权有条件、有边界的合法存续。国王的权能和王权的有限性根源于王权的合法性,权力渊源在赋予权力主体合法性的同时,也给定了其权力的内容和边界。
关于王权的合法性,布拉克顿继承并发展了王权神授观念,多次声明“法律使国王成其为国王,无法律之处则无国王”。布拉克顿的王权神授观念贯穿于王权的产生、行使以及对其最终的评判等方面。首先,王权源于上帝神权的授予,王权是神权的一部分。布拉克顿强调国王受上帝的恩赐,王权源于上帝。“任何正义的审判不是由人做出,而是来自上帝,因此国王的善治之心在上帝手中。”其次,王权要依上帝意志而行使。布拉克顿认为“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所以他必须明辨权利和侵权(合法与非法)、公正与不公正,由此所有臣民方可信靠其统治,正直诚实地生活于宁静与和平之中,彼此之间没有偷窃、抢劫、伤害以及杀戮”(24)。这表明万民顺从国王其实是顺从上帝的意志,以保障正义行于世间,和平得以存续。再次,对王权最终的价值判断的权力属于上帝。布拉克顿认为国王的行为不受任何人约束,只等待上帝的裁判。如国王一意孤行,上帝会严厉惩罚他。显然,布拉克顿主张上帝会审判和惩罚不能维持正义与和平的暴君。进而,布拉克顿从上帝“善”的价值取向上否定了暴君统治的合法性,即“暴君不再是上帝的臣子和代理人,而是魔鬼的代理人”(25)。在布拉克顿看来,国王只有持守正义之时才是上帝的代理人,一旦走向非正义、用暴力统治其民众时,其王权就失去了合法性。这是布拉克顿对先前存在的王权神授观念的创造性阐释,为臣民反抗暴君确立了神圣的法理依据。
布拉克顿还主张王权基于法律而产生。在他看来,“法律使国王成其为国王,如国王不依法律而统治,国王必须将法律赋予的权力归还法律。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国王”(26)。这表明王权除了上帝授予之外,还有法律这一合法性渊源。关于何谓法律,布拉克顿认为上帝是正义之源,法律基于上帝的意志而产生,以规范人和万物各得其所,从而实现持续而永恒的正义(27)。此外,习惯也是久已适用的法律(28)。
关于国王权能的观念主要体现在布拉克顿对国王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论述上。布拉克顿主张,没有广泛的同意,国王则不能变更或订立法律。“尽管国王的意志具有法律效力,但并非任何事情都依国王意志轻率而行。国王必须咨询贵族,经过商讨之后才能订立新法。”(29) 可见,布拉克顿不赞同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而亨利二世时期的大法官格兰威尔则明确主张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30)。格兰威尔的这一观念不仅源于亨利二世时期的强势王权,也是12世纪罗马法复兴使然(31),“乌尔比安所说的‘皇帝的命令具有法律的效力’这一国王高于法律的理论并没有静默、湮灭”(32)。到了亨利三世时代,布拉克顿则认为立法须经国王和贵族共同商议、反复推敲之后才能完成,只是由国王赋予其效力而已,国王单独立法没有合法性。
布拉克顿尽管认为国王和教会司法权彼此界限分明,但在世俗领域国王拥有固有司法权(ordinary jurisdiction),诸法官只拥有委任司法权(delegated jurisdiction),其权力必须由国王授权方具合法性。具有委任司法权的法官无权审理所有案件,只能有选择地审理某一部分案件(33)。显然,布拉克顿主张国王在世俗领域享有最高司法权,法官由国王选择和任命,并授予特定的司法权,法官的产生及其司法权的合法性源于国王的固有司法权。
关于王权的有限性,布拉克顿反复强调王权在合法存续期间要受到上帝与教会以及法律与贵族的限制。首先,王权要受到上帝与教会的限制。王权从产生到行使,直至对其最终的价值判断都在“上帝之下”。在中世纪英国,国王与臣民对基督教信仰有着高度的认同,这是王权受到上帝的限制具有实质意义的基础。王权受到上帝的限制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王权要受到教会的限制。布拉克顿多次主张在属灵的诉讼中,世俗的法官既没有司法权,也没有对判决的执行权,这一司法权属于统治和保护神职人员的教会法官。世俗诉讼的司法权属于国王,教会法官不得干预(34)。可见,布拉克顿认为教俗司法权彼此分离,二者之间有明确的界限,法官也有严格的区分,国王的司法权受到教会的限制。
其次,王权要受到法律与贵族的限制。布拉克顿主张“国王除依法行事之外,不得做任何事”(35)。而且他认为,“善治其国者需要法律和武力,二者兼具,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皆可达于秩序。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如果武力不足以对抗敌人,王国则失去防卫;如果国王不能有效地实施法律,正义将不复存在,将没有人可以给予公正的判决”(36)。显然,布拉克顿认为王权必须善用武力并依法而治,以维护王国的秩序和正义。王权受到法律的限制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王权受制于贵族。蒂尔尼在解读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时谈到,贵族通过咨议会对国王加以限制并非不可能。在现实中,国王要维持罪恶的不公平状态或者宣布非正义之事,是行不通的(37)。
综上所述,在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中,王权的合法性是王权的基础,国王的权能是王权的内在结构,而王权的有限性则是王权的外在边界。王权的合法性决定了国王的权能和王权的有限性。以往学者大多着眼于王权的外在边界即王权的有限性,而忽视了王权的基础和内在结构;这就使得对王权有限性的认识不够深入,从而使人们对布拉克顿王权观念历史影响的理解受到了限制。
三
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体现了他对13世纪英国社会政治状况的理解与思考。布拉克顿时代,英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普通法司法体系,传统的司法让位于王室法庭(38)。这是王权得以集中的结构性力量,从而实现了对王国较为有效的统治(39)。然而,教会力量和世俗王国并存,再加上封建贵族依靠传统特权及其掌握的社会力量,利用法律长期抵制王权的膨胀,从而限制了王权的过分集中。由此,布拉克顿提出了“国王在任何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的论断,为后世英国宪政的发展确立了有限王权原则。
在布拉克顿之后,爱德华二世和理查德二世皆被议会废黜(40)。显然,这一时期王权更加受制于贵族。因此,15世纪英国法学家福蒂斯丘在论述王权时多次引用布拉克顿所说的“法律使国王成其为国王,国王在法律之下”的原则,阐明英国国王不是绝对君主(41)。经过英法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封建贵族力量衰落了。及至都铎时期,1536年和1539年议会分别通过了《解散小修道院法案》与《解散修道院法案》,这两项法案明令修道院包括土地和其他财产都要交予国王和其继承人,此后解散了英国几乎全部的大小修道院。亨利八世为了对外战争变卖了得自教会的地产,通过贸易崛起的士绅阶层获得了其中大部分土地(42)。这导致了教会的衰落和乡绅的成长。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17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43)。同时,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海外贸易商人成为仅次于贵族的社会阶层,他们依靠购买爵位和官职等方式逐渐壮大(44)。可见,长期的战争消耗了贵族的财富和有生力量,宗教改革瓦解了教会的经济基础,乡绅和商人阶层等力量迅速成长,孕育了资产阶级。这为英国近代宪政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在封建贵族和教会衰落的同时,都铎王朝先后设立了各种特权法庭(45)。实质上,这是在独立的普通法体系之外建立直接由国王控制的司法体系,在此基础上王权逐渐得以强化。但以乡绅和商人为主的新兴资产阶级推动了议会下院的发展,都铎时期成为英国议会史上下院人数增长最多的时期,下院逐渐成为限制王权的主要力量(46),这使得“国王在法律之下”的传统并未归于沉寂。1539年议会通过的《公告法》授予国王颁布公告的权力,明示国王公告和议会法令具有同等效力,但公告必须由国王和枢密院共同拟订,且不得与既有的议会法令和普通法相抵触(47)。显然,国王在获得发布公告权时仍然受到了枢密院和议会以及既有法律的限制。而且由于下院的成长,都铎时期最终形成了“王在议会”的有限王权原则(48)。
斯图亚特时期,秉持苏格兰绝对王权传统的詹姆斯一世无视英国的有限王权传统,极力压制普通法法庭的司法活动,他本人甚至曾欲作为法官直接审理诉讼,并倡导英国法律的法典化(49)。詹姆斯一世的行为遭到以爱德华·科克为首的普通法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强烈反抗,科克重申布拉克顿的“国王在任何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的王权观念,来抵制詹姆斯一世对普通法司法的干预(50)。在新兴资产阶级限制王权的要求下,科克所倡导的“国王要在法律之下”在议会下院中得到支持。他们以议会为阵地与国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且反复强调国王的命令和行为不得违背法律,如果国王的特许状与法律相抵触将归于无效(51)。他们坚持王权与臣民自由之间的界限由普通法和议会法令确立,法官必须公平对待穷人和富人,在做出裁判之时要忽视国王的命令(52)。显然,新兴资产阶级立足于下院,依靠普通法和议会法令极力主张国王要在法律之下,以抵制王权的膨胀。1628年,科克主持起草了《权利请愿书》,并最终迫使国王查理一世签署了这一旨在限制王权与保障臣民自由权利的法案(53)。《权利请愿书》实际上成为1689年《权利法案》的先导。
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限制王权实现法治的要求,经过科克等人的重新阐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了创造性地转化,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强势王权以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旗帜。国王要在法律之下,即国王权力源于法定,其权力获得现实合法性的同时具有严格的界限;国王如果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使权力,任何臣民得依据现存法律维护其自由和权利。在法律之下对权力的约束和对权利的保障正是英国近代宪政的本质。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成为英国近代宪政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注释:
① F. 波洛克、F. W. 梅特兰:《英国法律史》(Sir Frederick Pollock and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版,第206—207页;亨利·莱维·于尔曼:《英国法律的传统》(Henri Lévy Ullmann, The English Legal Tradition),伦敦1935年版,第133—134页。
② F. 波洛克、F. W. 梅特兰:《英国法律史》第1卷,第206页;H. G. 理查德森:《阿佐、德罗伊达与布拉克顿》(H. G. Richardson, “Azo, Drogheda, and Bracton”),《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59卷,1944年第233期,第27页。
③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George E. Woodbine, ed., Bracton on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第2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33页。
④ 国内学者马克垚、孟广林、阎照祥、蔺志强、李红海等皆认为“王权有限性”限于观念层面,缺乏实践基础。参见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孟广林:《中古西欧的“法大于王”与“王在法下”之辨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阎照祥:《中英君主制的几点区别》,《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蔺志强:《13世纪英国的国王观念》,《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李红海:《普通法的历史解读——从梅特兰开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国外学者斯塔布斯、梅特兰、埃尔顿、舒尔茨、蒂尔尼、理查德森等多强调布拉克顿对英国法律和法学的贡献,他们涉及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时,也限于王权的有限性这一方面,具体参见本文相关引述。
⑤ 爱德华·科克:《英国国王史》(Edward Coke, The History of the Successions of the Kings of England),伦敦1682年版,第5页。
⑥ 詹姆斯·希思:《英国国王的生平与统治编年史》(James Heath, Englands Chronicle, or, The Lives and Reigns of the Kings and Queens),伦敦1699年版,第65—66页。
⑦ 艾伯特·毕比·怀特:《英国宪政的形成》(Albert Beebe Whit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伦敦1925年版,第256—258页;威廉·斯塔布斯:《英国宪政史》(William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03年版,第532—533页。
⑧ 艾伯特·毕比·怀特:《英国宪政的形成》,第258—263页。
⑨ 爱德华·科克:《英国国王史》,第9页。
⑩ 詹姆斯·希思:《英国国王的生平与统治编年史》,第102—107页。
(11) 卡尔·斯蒂芬森、弗雷德里克·乔治·马钱姆编:《英国宪政史文献》(Carl Stephenson and Frederick George Marcham, eds., Source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伦敦1937年版,第115—126页。
(12) 哈里·罗斯维尔主编:《英国历史文献,1189—1327》(Harry Rothwell,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89-1327),伦敦1975年版,第32—33页;D. A. 卡彭特:《英国封建主义的第二个世纪》(D. A. Carpenter, “The Second Century of English Feudalism”),《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168卷,(2000年)第36页。
(13) 哈里·罗斯维尔主编:《英国历史文献,1189—1327》,第361—367页。
(14) 从1066年到1166年军役采邑提供的是真正的军役,然而,从1166年到1266年军役采邑主要以缴纳盾牌钱来供养国王的军队。F. 波洛克、F. W. 梅特兰:《英国法律史》第1卷,第252—253页。
(15) 威廉·斯塔布斯:《英国宪政史》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896年版,第258页。
(16) 朱寰:《略论中古时代的君权与教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17) 约翰·福蒂斯丘:《绝对王权与有限王权之间的差异》(Sir John Fortescu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bsolute and Limited Monarchy),伦敦1714年版,导言第21页。
(18) 约翰·福蒂斯丘:《绝对王权与有限王权之间的差异》,导言第26—28页。
(19)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33、110、306页。
(20) 约瑟夫·斯特拉耶主编:《中世纪辞典》(Joseph R. Strayer, ed.,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第7卷,纽约1989年版,第264—266页;舒尔茨:《布拉克顿论王权》(Fritz Schulz, “Bracton on Kingship”),《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60卷,1945年第237期,第162—165页。
(21)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论政府原理》(John of Salisbury, Policraticu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190—216页。
(22) 约翰·内维尔·菲吉斯:《论王权神授》(John Neville Figgis,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剑桥大学出版社1914年版,第19页。
(23)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20、33、166、305页。
(24)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305、20、166页。
(25)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109—110、33、305页。
(26)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33页。
(27)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22—23页。
(28)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21—22页;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83—84页;R. H. 赫姆霍尔兹:《圣杰曼与习惯法》(R. H. Helmholz, “Christopher St. German and the Law of Custom”),《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第70卷2003年第1期,第134页。
(29)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305页。
(30) 格兰威尔:《格兰威尔著作选译集》(A Translation of Glanville),华盛顿1900年版,导言第17页;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9页。
(31) 亨利·莱维·于尔曼:《英国法律的传统》,第176—180页,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格兰威尔受到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影响。
(32) J. M. 凯利著,王笑红译:《西方法律思想简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33)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304—306页。
(34)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4卷,第250—251、281、298页。
(35)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305页。
(36) 乔治·E. 伍德拜因编:《布拉克顿论英国法律与习惯》第2卷,第19页。
(37) 布赖恩·蒂尔尼:《布拉克顿论政府》(Brian Tierney,“Bracton on Government”),《中世纪研究》(Speculum)(1963年)第38卷第2期,第316页。
(38) F. W. 梅特兰:《英国宪政史》(F. W. 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剑桥大学出版社1919年版,第18页。
(39) 在同时代的法国,法律和司法都是极为分散和混乱的,王权之下的司法局限于国王领地之内。S. J. T. 米勒:《布拉克顿和博马努瓦的国王地位观》(S. J. T. Miller, “The Position of the King in Bracton and Beaumanoir”),《中世纪研究》第31卷1956年第2期,第296页。
(40) 詹姆斯·希思:《英国国王的生平与统治编年史》,第127—128、144—146页。
(41) F. W. 梅特兰:《英国宪政史》,第198页。
(42) 《王国法令集》(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第3卷,布法罗1993年版,第575—578、733—739页;肯·鲍威尔、克里斯·库克主编:《英国历史实录,1485—1603》(Ken Powell and Chris Cook eds., English Historical Facts, 1485-1603),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88页。
(4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8页。
(44) 张乃和:《大发现时代中英海外贸易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2页。
(45) 《王国法令集》第2卷,第509—510页;第3卷,第569—574、798—801页。
(46) 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6页。
(47) 《王国法令集》第3卷,第726—728页。
(48) G. R. 埃尔顿:《都铎宪政文献与评论》(G. R. Elton, The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262页。
(49) 詹姆斯一世:《国王詹姆斯一世著作集》(The Workes of the Most High and Mightie Prince Iames),伦敦1616年版,第512页。
(50) 爱德华·科克:《判例汇编第十二编》(The Twelfth Part of the R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伦敦1658年版,第63—65页。
(51) 乔伊斯·李·马尔科姆:《不为非:法律、自由及对国王的限制》(Joyce Lee Malcolm,“Doing No Wrong: Law, Liberty, and the Constraint of Kings”),《不列颠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第38卷1999年第2期,第164—165页。
(52) 乔伊斯·李·马尔科姆主编:《主权之争:17世纪英国政治文献集》(Joyce Lee Malcolm ed., 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racts),美国自由基金公司1999年版,导言第23—27页。
(53) 《王国法令集》第5卷,第23—25页。
转自《世界历史》(京)2009年1期第84~91页
责任编辑:刘悦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上一篇:论都铎英国的货币管制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