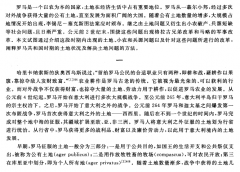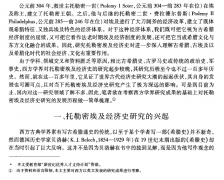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
作者简介:
刘琳琳
【英文标题】Concept of Supernatural Beings in the National Gods-sacrificing System of Ancient Japan
【作者简介】刘琳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是日本古代国家神祇祭祀体系中的与疫病有关的祭祀。本文主要是分析这三个祭祀中蕴含的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镇花祭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神作祟”观念,道飨祭是一个混合了中日两种文化因素的祭祀,一方面其思想依据是鬼魅、特别是中国的疫鬼观念;另一方面,道飨祭对于鬼魅的态度并非中国式的暴力威胁,而依然采取日本原有对待神的恭敬态度。疫神祭中的“疫神”则是把中国的疫鬼改造为日本式的“神”,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信仰的话语体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疫病祭祀的角度对三个祭祀进行整体把握,发现道飨祭和疫神祭的鬼神观念均来源于中国的“疫鬼”,以及日本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的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
【关 键 词】疫病祭祀/镇花祭/道飨祭/疫神祭/疫鬼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医学基本术语“传染病”和“流行病”,在我国传统上有多种表述,比如“疫”、“疫疠”、“瘟疫”、“疫病”等。为了行文简洁,本文统称为“疫病”。自古至今,人类一直无法逃避疫病的威胁,翻开中外史书,那一条条关于疫病的记载的背后,有多少生命被无情吞噬。而人类也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应对疫病,既有纯粹医学意义上的治疗,也有宗教(包括巫术)的手段。正如俗语所说的“临时抱佛脚”,即使在医学发达的现代,面对防不胜防的传染病,很多人还免不了求神拜佛。如今,在医学不发达的地区,宗教手段往往还成为人们克服疾病的必然选择,甚至连国家政权都不能拒绝。古今东西,关于疫病的祈祷、驱除仪式不可胜数,从中可以透视出人们多样的疫病观念,比如对影响人类生存的超自然力量的认知和应对措施等。可以说,应对疫病的仪式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本文集中探讨日本古代国家应对疫病的仪式。之所以使用疫病祭祀这样的表述,是因为日本古代关于疫病的仪式有很多,既有神道性的祭祀,也有佛教性的读经、仁王会等。本文聚焦于神道性的祭祀,具体来说是《延喜式》中“神祇式”部分记载的三个与消除疫病有关的、由神祇官①主管的祭祀——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笔者把三者统称为疫病祭祀。
《延喜式》是10世纪初由当时日本朝廷编修的一部重要法典,由天皇的外戚藤原时平、藤原忠平领衔主持编写。这部法典对此前颁布的《养老律令》、《弘仁式》等律令格式进行了很好的归纳整理,体例完备,堪称自大化改新到10世纪初期二百多年间日本律令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今人研究日本古代制度史和文化史的基础史料。古代日本在法制建构过程中,一向重视祭祀神祇。例如,按照目前日本史学界通行的说法,701年编纂的《大宝令》中就已经有专门涉及朝廷神祇祭祀的“神祇令”,其中规定了朝廷每年在固定时间必须举行的一系列祭祀,如祈年祭、风神祭等等,形成了按照岁时执行的祭祀体系,由此体现出古代天皇制国家在宗教祭祀方面的特征。757年开始实施的《养老令》基本延续了《大宝令》关于神祇的规定。而《延喜式》中的《神祇式》部分,一方面继承了《大宝令》的祭祀体系,同时又反映了8、9世纪之间祭祀领域的新变化,因此其丰富程度远超过《大宝令》和《养老令》,体现出日本古代国家祭祀体系的整体面貌。目前,日本史学界一般把《延喜式》中的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视为与疫病直接有关的祭祀。
日本目前对于这三个祭祀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对各个祭祀进行分别探讨,而不是从三者同属疫病祭祀这个大的视角进行整体把握。其中,镇花祭的研究最为薄弱,仅有西田长男的《镇花祭一斑》②等寥寥数篇论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有关镇花祭的资料非常少。关于道飨祭和疫神祭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一些,研究的重点大致有两个,第一是道飨祭与疫神祭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战前的祝词研究者次田润的观点影响较大。他认为,道飨祭就是疫神祭,“道飨祭总是具有疫神祭的性质,作为恒例举行的是道飨祭,临时举行的就是疫神祭”③。他的主张现在依然被广泛接受。第二是道飨祭的祭祀对象问题。如后文所述,在奈良到平安时代,关于道飨祭的祭祀对象和防范对象是什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如《令释》的资料显示道飨祭的祭祀对象、同时也是防范对象为“鬼魅”,而《延喜式祝词》则表明道飨祭的祭祀对象是守卫路口的神,防范对象是来自冥界的“害人之物”。从江户时代一直到今天,不少学者注意到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对此也做过诸多诠释,他们围绕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哪个是本源、哪个是变型的问题展开过许多争论,但至今依然是意见纷纭,令人困惑。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疫病祭祀这个大的框架整体把握以上三个祭祀,重点考察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以下简称“疫病鬼神观念”),包括鬼神观念的演变脉络以及与中国的疫病鬼神观念的联系。
二、镇花祭与神灵作祟观念
根据日本学者考证,《大宝令》中就已经有了关于镇花祭和道飨祭的规定④。《养老令》中的“神祇令”部分按照季节顺序罗列祭祀名称,如仲春的祈年祭、孟夏的神衣祭等,共有19个祭祀,但没有对这些祭祀进行更多的解说。镇花祭也是其中之一,放在“季春条”,由此可知该祭祀举行时间为季春,即阴历三月。《延喜式》把朝廷祭祀分为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举行的“四时祭”和没有固定时间的“临时祭”两个类型。镇花祭属于四时祭,在3月晦日举行,祭祀的对象是“大神社和狭井社”。大神社是位于今奈良县樱井市的大神神社,祭祀的神是大物主神(又名大国主神、大己贵神),狭井社祭祀的是大物主神的“武魂”(日语原文为“荒魂”)。镇花祭由来于崇神天皇时期大物主神作祟引发疫病的传说。《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对这则传说都有记载,其中《日本书纪》比较详细。其大致情节是:崇神天皇五年,“国内多疾疫,民有死亡者,且大半矣。”到了崇神七年,天皇占卜疫病的起因,占卜过程中大物主神通过附体的方式降下神谕,称:“天皇何忧国不治也?若能敬祭我者,必当自平矣!”此后,天皇夜里又梦见大物主神,“是夜梦,有一贵人,对立户殿,自称大物主神,曰:‘天皇,勿复为愁。国之不治,是吾意也。若令吾儿大田田根子祭吾,则立平矣。亦有海外之国,自当归服’。”同年11月,崇神天皇依言“以大田田根子为祭大神之神官”,于是疫病逐渐消除⑤。在这则传说中包含的疫病起因观念是神的意志引发疫病,这本质上属于神灵作祟信仰的一个表现⑥。神灵作祟信仰是古代神道教中的重要观念,即认为神会做出危害人类的事情,这称为作祟,个别人或者大规模人群生病、地震、火山爆发、水旱灾害等,都可以被解释为神的作祟。人们认为神作祟的原因在于没有受到足够隆重的祭祀,因而怒气爆发,惩罚人类。神灵作祟观念是人类智识不发达、面对自然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受自然支配的表现,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用奉献供品、恭敬的礼拜祈祷来乞求神灵停止作祟,从而消除疫病和灾害,保佑众生的生命。这属于较早的信仰形态,因此可以说镇花祭反映的是较早的疫病观。
大物主神作祟制造疫病的传说不止于此。《古事记》记载,垂仁天皇时期,皇子品牟都从小是个哑巴,垂仁天皇十分发愁。一天夜里梦见有神对他说:“若修建如皇宫般壮丽的宫殿来供奉我,此皇子必定会开言。”垂仁天皇经过占卜,得知“此祟乃出云大神之御心”⑦。出云大神就是大物主神。这则传说的情节几乎和崇神时期的作祟传说一模一样,都是天皇遇到不易解决的困难,梦中有不知名的神要求给予隆重祭祀,醒来经过占卜,发现是大物主神作祟。在记纪神话⑧中大物主神是素盏呜尊的子孙,出云国⑨的国主神,在天孙降临到地上世界并准备建立一统江山的时候,大物主神和他统治的出云国被视为障碍,最终以天孙方面供奉祭祀大物主神为条件,不太情愿地让出了出云的统治权。这当然都只是神话传说。日本史学界通行的说法认为,出云势力本来是大和政权的异己力量,构成大和政权扩大统治范围道路上的绊脚石,“让国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出云势力被迫屈服的历史。大物主神两次要求得到高规格的祭祀待遇,可以看作出云势力与大和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神话中的投影。
到了平安时代,9世纪初期,关于镇花祭的理解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编纂于833年的《令义解》对镇花祭的解释是:“谓大神、狭井二祭也。在春花飞散之时,疫神分散而行疠。为其镇遏,必有此祭,故曰镇花。”⑩《令义解》是当时朝廷编纂的对《养老令》的解释性文献,看来此时官方已经把大物主神视为疫神。这大概与每年都定期祭祀这个容易制造疫病的神有关,天长日久,人们就把他称为疫神。春季由于天气转暖,是传染病的高发期,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古代日本人从季春时节花瓣凋落的现象出发,产生了疫神随着飘飞的花瓣而散播疫病的观念。
三、道飨祭与中国的疫鬼观念
道飨祭和镇花祭一样,在《大宝令》的祭祀体系中已经存在,也属于每年在固定时间举行的四时祭,日期为六月、十二月的晦日。《令义解》、《令集解》中的相关解释以及《延喜式》祝词部分中收录的道飨祭祝词是关于道飨祭的基本史料。《令义解》成书于9世纪30年代,属于官方文献,其中的解释是:“谓卜部等于京城四隅道上而祭之。言欲令鬼魅自外来者,不敢入京师。故预迎于道而飨遏也。”(11)《令集解》成书于868年前后,是明法博士惟宗直本个人编写的,并非官方文献。其中对道飨祭的解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完全抄录《令义解》的说法,另一部分则引用了《令释》的说法:“释云:京四方大路最极,卜部等祭,用牛皮及鹿、猪皮也。此为鬼魅自外莫来宫内而祭之。左右京职参与。《古记》无别。”(12)此处的“《古记》”,是一部对《大宝令》的解释性文献,738年左右成书,编者不详,且原书久已散佚。所谓“《古记》无别”,意思是《古记》中也持同样的看法。《令释》是对养老令的解释性文献,成书于约787年至791年之间。因此在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道飨祭的解释中,《古记》的说法是最早的。上述几部令的解释书显示出道飨祭仪式形态的一些特点,比如主持道飨祭的神职集团是隶属于神祇官的卜部(13),举行的地点是在京城四角的道路上,祭祀需要使用猪皮、鹿皮等动物皮。日本学者认为用兽皮作为祭品是中国古代祭祀的习惯,即道飨祭吸收了中国祭祀文化的因素(14)。
但是延喜式祝词描写的道飨祭情况与几部令的解释书明显不同。其内容翻译为现代汉语大意如下:“面对宛如巨岩磐石一样镇守八衢的大神,臣等惶恐谨白:名叫八衢男神、八衢女神和久那斗神的诸位神祇,若遇到来自根国底国的凶猛害人之物,不要纵容,不要与他们说话,不要放他们进来。他们从下边来就守住下边,从上边来就守住上边。祈求大神日夜守护与祝福。”(15)
《延喜式》祝词中记载的祈祷对象是镇守各个路口、有具体名字的三个神,人们向这三个神祈祷,希望他们拦截“来自根国底国的凶猛害人之物”。而按照《古记》、《令释》等的条文,道飨祭的祈祷对象是“鬼魅”,目的是不让鬼魅从外部进入宫中或者京城,采用的方法是“飨遏”鬼魅,即用酒食款待的方式阻止“鬼魅”,与守卫路口的神无关。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区别。
笔者在本文不打算继续这个争论,而是转向探讨道飨祭与疫病的关系。日本学者往往不假思索就把道飨祭视为祈祷消除疫病的祭祀。笔者反对这样的观点,认为道飨祭本来是一个消除广义的危害因素的祭祀,只要仔细读一下相关史料就可以确认这一点。祝词显示其针对的是“来自根国底国的凶猛害人之物”。这里所谓的“物”,根据次田润的解释,是指“包括邪神恶灵在内的所有妖鬼”(16)。很明显,这不局限于疫病制造者,而是泛指一切危害人类的因素。而《令义解》中的“鬼魅”,也是一个比较含混的说法。10世纪初期贵族源顺编写的辞典——《倭名类聚抄》的“鬼神部”就有专门的“鬼魅类”一条,其中罗列了八种鬼魅,分别是饿鬼、疟鬼、邪鬼、穷鬼、魑魅、魍魉、丑女和天探女。其中饿鬼概念来自佛教,疟鬼、穷鬼、魑魅、魍魉是中国的鬼怪概念,邪鬼、丑女和天探女则是日本书纪中出现的对人或者神构成威胁的存在。这其中真正与疫病有关的只有“疟鬼”。而《倭名类聚抄》对“疟鬼”的解释是摘抄了东汉蔡邕的《独断》:“蔡邕《独断》云,昔颛顼有三子,亡去而为疫鬼。其一居江水,是为疟鬼(和名衣也美乃加美或於尔)。”(17)可见在奈良至平安时代,“鬼魅”一词所指甚广,其中包括与疫病有关的鬼;道飨祭本来针对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危害人类生活的超自然存在,并非专门应对疫病。目前已知的日本古代较早的直接应对疫病的国家性祭祀就是镇花祭。
道飨祭原本固定在六月、十二月晦日举行,不过奈良时代,在发生大规模疫病的时候,作为抗病救灾的一个环节,也临时举行道飨祭。天平七年(735年)八月乙未(四日),针对在太宰府(今九州的福冈县境内)发生的严重疫病,圣武天皇发了一道敕令。“敕曰:‘如闻:比日,大宰府疫死者多。思欲救疗疫气,以济民命。’是以,奉币彼部神祇,为民祷祈焉。又府大寺及别国诸寺,读金刚般若经。又其长门以还诸国守、或介,专斋戒、道飨祭祀。”(18)对于远在太宰府的这一次瘟疫,古代国家动用了多种宗教手段,包括向太宰府管辖内的神灵进献币帛举行祈祷,佛教方面有组织读经,举行道飨祭也是诸多应对措施之一。其实施的场所是在“长门以还”。长门是今山口县西部、南部地区的古称,“以还”日语训读为“よりこのかた”(yorikonokata),即把发生疫病的太宰府视为“外部”,长门以北靠近京都、尚未蔓延疫病的地区视为“内部”。朝廷命令这些内部各个国的国守、介等官员,举行道飨祭,意在拦截疫病,使之局限在太宰府一地。如此看来,道飨祭本来的针对对象比较宽泛,所以在疫病多发的时期,可以应用于疫病祈祷。7、8世纪左右,随着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体制的逐步建立,交通条件的改善,人口向都城集中等等,疫病的爆发也呈现空前的态势,应对疫病成为日本古代国家面临的紧要课题,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在疫病中求生存。于是,原本驱除对象比较广泛的传统祭祀道飨祭被应用于疫病祈祷,这是传统祭祀文化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一种表现。
道飨祭专门用于拦截疫病,其观念基础在于“鬼魅”中包括的与疫病有关的鬼。《倭名类聚抄》对鬼魅的解释中共有两个词与疫病有关,一是“疟鬼”,即专门引发疟疾的鬼。二是“疫鬼”,这个词虽然没有作为词条列出,但是出现在“疟鬼”一词的解释中,根据文意,应该指引发疫病的鬼。这也表明此时的日本对于疫病起因有了新的认识,即从中国引进了“鬼制造疫病”的观念。中国从战国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鬼制造疫病”的意识。比如汉代刘熙的《释名》对“疫”这个字的解释是:“疫,役也,言有鬼行疾也。”④中国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疫鬼”、“厉鬼”、“疠鬼”、“疾疠之鬼”等词汇。比如有着悠久历史的仪式——傩,其目的就是驱除带来瘟疫的鬼。《论语·乡党》中有“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何晏在《论语注疏》中引用西汉孔安国语:“孔曰:‘傩驱逐疫鬼,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20)孔安国提到疫鬼一词,表明西汉时期知识阶层已经熟知疫鬼的存在。另外,大约东汉时期开始,颛顼的三个儿子变成疫鬼的说法广为流传,东汉时期卫宏的《汉旧仪》、王充的《论衡》、蔡邕的《独断》、晋人干宝的《搜神记》对此都有记载,只是个别字句有所出入。南朝民间也流传着旱疫鬼的传说。例如,《隋书·五行志》记载:“梁太清元年,丹阳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顶上,大如两岁儿,坠地而言曰:‘儿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当令我得过。’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绛帽,故当无忧’。”(21)唐朝文人李邕(679-748年)在《金谷园记》中也写道:“阴气将绝,阳气始来,阴阳相激,化为疾疠之鬼,为人家作病。”(22)可见自汉至唐一千年间,疫鬼制造瘟疫的信仰在中国社会可谓根深蒂固。
古代日本在积极吸纳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接受了中国的疫鬼、疠鬼概念,同时也引进了驱除疫鬼的傩仪式。目前已知日本宫廷举行傩的最早记载是在706年(庆云三年),这一年由于京畿、纪伊等许多地方接连发生疫病,朝廷采取了各种办法试图消除疫病,其中就包括大傩。“天下诸国疫疾,百姓多死。始作土牛大傩。”后来傩成为朝廷每年十二月晦日举行的常规性仪式,由阴阳寮主持。《延喜式》以及9世纪前半叶成书的《贞观仪式》都有专门的大傩条。《贞观仪式》的十二月大傩部分收录了阴阳师念诵的祭文,显示驱除对象就是“秽恶之疫鬼”(23)。11世纪早期明法博士惟宗允亮编写的《政事要略》一书,对于追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说,该书大量引用《周礼》、《论语注疏》、《汉旧仪》等关于大傩的说明,其中也包括有关疫鬼的内容。比如引用《论语疏》的解释:“乡人傩,傩者逐疫鬼也。”又引用郑玄的说法:“郑玄云,此傩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疠鬼随之出行。”(24)该书还画出疫鬼的形象,半裸,仅穿红色兜裆布,头发竖直,骨骼嶙峋,怒目圆睁,身上长毛,每只脚的脚趾只有两个,且长着利爪(25)。此外,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八月朝廷发布的敕中提到,由于翌年为不祥的“三合”之年,会“有水旱疾疫之灾”,故提倡官民都要念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心经”。理由是“天子念,则兵革灾害,不入国里。庶人念,则疾疫疠鬼,不入家中。”(26)而774年(宝龟五年)夏四月十三日(己卯)又一次发布应对疫病的敕,同样倡导念诵该经,其理由与上述语句几乎一模一样:“天子念之,则兵革灾害不入国中。庶人念之,则疾疫疠鬼不入家内。”(27)由此可以判断,古代日本国家接受了中国的疫鬼、疠鬼观念。疫鬼、疠鬼观念成为奈良朝廷应对疫病举措的重要思想依据之一,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多种规避疫鬼的办法,比如有中国式的大傩、佛教式的读经。道飨祭也是以引进疫鬼观念为背景,由原来笼统地应对各位威胁因素的祭祀转变为主要应对疫病的祭祀。
四、疫神祭与疫鬼观念的日本化
在奈良时代初期《养老令》规定的国家祭祀体系中本来没有疫神祭,目前史料中最早的疫神祭见于奈良时代晚期的770年代即光仁天皇在位的宝龟年间,这段时期频繁举行疫神祭。现把《续日本纪》中宝龟年间出现的疫神祭记载列举如下:
770年(宝龟元年)六月甲寅条:祭疫神于京师四隅、畿内(28)十界。
771年(宝龟二年)三月壬戌条:令天下诸国祭疫神。
773年(宝龟四年)秋七月癸未条:祭疫神于天下诸国。
775年(宝龟六年)六月甲申条:遣使祭疫神于畿内诸国。
775年(宝龟六年)八月癸未条:是日,祭疫神于五畿内。
777年(宝龟八年)二月庚戌条:遣使祭疫神于五畿内。
778年(宝龟九年)三月癸酉条:大祓,遣使奉币于伊势神宫及天下诸神,以皇太子不平也。又于畿内诸界祭疫神。
相对于镇花祭和道飨祭来说,疫神祭显然是光仁天皇时期出现的新的祭祀形态,在8世纪70年代频频举行,9世纪时仁明天皇在位的834年、837年、839年、842年以及清和天皇在位的852年、865年各举行过一次。延喜式把这个祭祀归类为临时祭,从而确立了疫神祭作为律令制祭祀体系之一员的地位。
《延喜式》规定的疫神祭种类有“宫城四隅疫神祭(若应祭京城,四隅准此)”、“畿内堺十处疫神祭”。从夹注来看,举行地点有三种,即宫城(皇宫及周围官衙所在的地区)的四角、京城的四角、畿内五个国之间以及畿内各国与相邻的畿外各国的十个交界处,如山城与大和交界处、大和与伊贺交界处等(29)。《延喜式》中没有在天下诸国举行疫神祭的规定,但上述史料显示古代国家会根据实际需要在全国举行疫神祭。
日本很多学者指出疫神祭和道飨祭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笔者认为,疫神祭是道飨祭的延伸与扩大。首先疫神祭与道飨祭的实施地点都是在边界上,都体现了在边界拦截疫病、守卫皇宫或者京城的意识(30)。只不过疫神祭实施的范围更广,远远超出了京都。而且举行的地点从天皇居住的皇宫即宫城的四角,到京城(光仁天皇时期是在平城京,后来迁至平安京)的四角,以及京都周边几个“国”之间的共十个交界处,这样就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三个防护圈。从举行时间来看,延喜式规定道飨祭是四时祭,每年固定在六月、十二月晦日两天举行。而疫神祭则是临时祭,可以根据疫病流行的具体情况随机实施。因此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来看,疫神祭可以说是道飨祭的延伸与扩大。这种扩大当然是出于应对频繁突发的瘟疫的需要。
疫神祭的祭祀对象——“疫神”,从文献分析看应该是奈良时代晚期出现的新概念。那么这个词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是疫病的制造者,还是驱除疫病的保护神呢?江户时代著名的国学者平田笃胤主张,疫神祭中的“疫神”指的是驱除鬼魅的“塞神”。他还特别指出:“世上有时把散播疫病的妖鬼叫作疫神,不要把两者混淆起来”,“再考虑到临时祭祀仪式里也有畿内边界十所疫神祭,就是因为他挡住八衢,有驱除散播疫病的鬼魅之功绩,所以称为疫神。”(31)平田笃胤还认为疫神祭的祭祀对象——疫神就是防疫之神,与道飨祭一样是指在十字路口驱除疫病因素的“塞神”。然而现代的日本学者多数把疫神当作一般名词来使用,泛指引发疫病的各种鬼神。
笔者发现,能够直接说明“疫神”性质的史料非常少,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判断疫神的性质。第一,《本朝世纪》正历五年(994年)六月十六日条记述:“今日妖言,疫神将横行,都人士女,不可出行云云。仍上卿以下至于庶民闭门户,无往还之辈。”(32)横行京城、吓得男女贵贱不敢自由外出的“疫神”,不大可能是把守边界、保佑人们生活的神,更像是散播疫病、危害人类生活的鬼神。第二,必须明确的是疫神祭中的疫神绝对不是《令义解》镇花祭条中说的“疫神”即大物主神,因为祭祀大物主神是在神社进行,而不是在国界或者皇宫京城等四角。第三,既然疫神祭的前身是道飨祭,而我们已经明确了道飨祭经历了从笼统地拦截各种鬼魅演变为专门针对疫鬼的转变,所以探讨疫神的性质时可以把疫鬼作为一条线索。
笔者认为,“疫神”一词其实是日本朝廷把中国的“疫鬼”观念日本化、“神”化,进而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话语体系的产物。
首先,日本古代存在着疫神就是冥界阎王派遣来的鬼的观念。编写于822年左右的传说集《日本灵异记》中卷第25篇记载了一个生病的女子因为用酒食贿赂鬼而得到帮助的故事,其中就存在“疫神等同于冥界的鬼”的观念。“赞岐国山田郡,有布敷臣衣女。圣武天皇时代,衣女忽得病。时盛备百味,祭门左右,赂于疫神而飨之也。阎罗王使鬼,来召衣女。其鬼走疲,见祭食,腼就而受之。”接受了祭飨的鬼为了回报,把另外一个乡的同名女子打死,带回阎王那里,但被阎王识破。最后编者景戒慨叹道:“备飨赂鬼,此功非虚,凡有物者,犹可赂飨。是亦奇异事矣。”(33)由此可见本故事中疫神指的就是来自阴间的鬼。这虽然是一则民间传说,但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的疫神概念就是来自冥界、散布疫病的鬼。把鬼称为“疫神”,显示出当时日本人对汉字“鬼”与“神”的意义区分并不十分清楚。
其次,从平安时代日本人对于汉字“鬼”的训读可以了解其鬼观念的特点。由于六国史都是用汉文体写作,除朝廷诏书以外没有标注日语读音,因此很难知晓“疫鬼”一词在当时究竟念什么。不过笔者还是从《倭名类聚抄》的“疟鬼”一条发现一些线索。《倭名类聚抄》对于“疟鬼”标注的和名是万叶假名“衣也美乃加美”,即“ぇやみのかみ”(eyaminokami),“ぇやみ”(eyami)是古代日语对“疫”或者“疟”的训读,“かみ”(kami)是“神”的训读,“衣也美乃加美”的意思直译就是“疫神”或者“疟神”,即古代日本人把中国的“疟鬼”理解为与疟病有关的神。这是依据日本的“神”(かみ)范畴来理解中国的疟鬼(34)。
第三,日本传统的神灵作祟信仰对于制造疫病的神采取祈祷、供祭态度,而中国的疫鬼观念中对于疫病制造的鬼采取的主要是暴力驱逐甚至“刑杀”态度,与日本原有的“神”观念不一致。比如,同样是以应对疠鬼为目的,中国的大傩和日本的大傩或追傩就存在差异。《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宫廷大傩中要唱杀气腾腾的“吃鬼歌”:“甲作食凶,肺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35)《大唐开元礼》第90卷大傩条中也收录了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歌词,可见对疫鬼毫不留情的态度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朝。而日本的大傩则温和的多。《贞观仪式》“十二月大傩仪”一条,收录了大傩的祭文。其主要部分是:“隐藏在处处村庄的秽恶之疫鬼,千里之外,四方之境,东方陆奥,西方远值嘉,南方土佐,北方佐渡以外,定为汝等疫鬼居住之处,今送汝等五色宝物、种种山珍海味,速速前去应去之处。以此驱赶(疫鬼)。若挟奸心,停留隐藏,则大傩公、小傩公持各种兵器追走刑杀。”(36)此处对待疫鬼的态度主要是送给疫鬼“五色宝物”,求其退到日本以外;如果疫鬼不听劝告,方才让大傩公、小傩公等“刑杀”之。而据三宅和朗等日本学者研究,日本大傩祭文中最后几句暴力追杀的部分在整个祭文中属于附加性的,不占重要地位(37)。大傩虽然是来自中国的驱鬼仪式,但日本却按照其传统的对待作祟之神的温和态度来对待疫鬼,对中国大傩进行了符合日本信仰传统的改造。再比如,道飨祭也是带有中国文化因素的祭祀,但对于鬼魅还是希望以“飨”求得“遏”的效果。延喜式祝词中虽然没有款待来自冥界的害人之物的说法,但也没有要“刑杀”的意思,只是请求镇守八衢的神不要和害人之物说话,拦住鬼魅的来路而已。至于疫神祭,有的日本学者,如笹生卫,主张疫神“很可能是被视为近乎‘追走刑杀’的对象而存在”(38)。但笔者认为这种观念找不到史料支持,该祭祀中对待疫神的态度也是以礼敬为主。这可以从以下史料窥知,一条是《续日本后纪》承和六年(839年)闰正月二十三日的敕命:“又令乡邑每季敬祀疫神。”另一条是《文德天皇实录》仁寿二年(852年)十二月丁亥(二十六日)的记载:“五畿内、七道诸国,请练行僧读金刚般若经,以资疫神。”日本古代文献一般把“资”训读为“たすけ”(tasuke),即帮助。对疫神“资”和“敬祀”,表明发布此命令的朝廷的态度还比较恭敬,没有剑拔弩张、“追走刑杀”的痕迹。还有《延喜式》疫神祭一条罗列了供奉给疫神的物品,主要有“倭文一丈六尺,木绵四斤八两,麻八斤,庸布八段,锹十六口,牛皮、熊皮、鹿皮、猪皮各四张,米、酒各四斗,稻十六束,鲍鱼、坚鱼各十六斤,二斗,滑海藻、杂海菜各十六斤,盐二斗”等。这么多的纺织品、海产品以及米、酒等送给疫神,其态度不能不说是恭敬礼貌。
由此可见,疫神祭的核心概念其实来源于中国的“疫鬼”。日本一方面引进了中国的疫鬼、疠鬼观念;另一方面却倾向于依据日本原有的神观念来理解疫鬼,把鬼叫作神,对待疫鬼也是沿用传统的尊敬、礼拜、祈祷的态度。这样就把制造疫病的鬼改造为“神”,并专门创造一个新的祭祀——疫神祭来供奉该神,充分体现了古代日本人对于超自然和超人的存在(无论是保佑人类的还是威胁人类的)都敬畏礼拜的态度。疫神祭可以说是日本吸收、改造中国疫病信仰文化,两种信仰相互融合的结果。
由于医疗手段落后,以及宗教信仰对人们精神的支配作用,日本古代国家在应对疫病时,非常重视采取宗教祭祀的方式。因此,在律令制国家体制建构过程中,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等三个祭祀被纳入国家法定的神道祭祀体系。这三个祭祀所蕴含的疫病观念、特别是对引发疫病的因素——鬼神的理解并不一样。镇花祭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神灵作祟观念,神对人类并非只是保佑,如果由于祭祀不周等原因得罪了神,神就会发怒,制造疫病或者各种灾害,惩罚人类。要想消除疫病,只能通过恭敬地祈祷来请求神停止作祟,保佑众生。道飨祭是一个典型的中日文化因素混合的祭祀,它受到中国疫病观念的影响,其思想依据是鬼魅、特别是中国的疫鬼观念。同时,道飨祭对于制造疫病的鬼魅并非采用中国式的暴力威胁,而是依然采取日本原有对待神的态度,即以酒食款待、祈求离去为主。疫神祭则把中国的疫鬼观念改造为日本式的“神”,将其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信仰的话语体系。从制造疫病的大物主神到疫鬼、再到疫鬼的“神”化,这一演变轨迹反映出日本古代神道文化一方面积极吸收中国的信仰观念与祭祀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放弃日本原有的“神”的概念话语以及对各种超自然存在的敬畏态度,从而形成了古代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错融汇的局面。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祭祀曾经是应对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的上述三个祭祀也不例外。那么这些疫病祭祀在日本古代发挥了怎样的社会功能呢?古人热衷于举行疫病祭祀,显然是希望借此祈求鬼神能消除疫病或者停止散播疫病,从而保证人类健康。但是现代医学早已证明,引发疫病的根本因素是细菌、病毒等客观存在的因素,而不是只在人类想象中存在的鬼神。因此举行再多的疫病祭祀也不可能消灭客观的致病因素,不可能真正发挥当事者所期望的控制疫病的功能。那么疫病祭祀完全是虚妄的、对人类没有任何益处的吗?也并非如此。祭祀手段的功能主要是针对人的心理层面。个人在患病时,是否有着战胜疾病的心理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亚于纯粹的医学治疗。个人如此,一个社会在遭受大规模疫病袭击时也同样需要足够的心理支持,而且越是在医疗手段落后的时代,社会越是需要这种心理上的鼓励。日本古代国家举行疫病祭祀,通过与神鬼的沟通交流来表达人的愿望,可以使人在精神上获得慰藉与鼓舞,增强应对疫病的信心与勇气。因此,笔者认为疫病祭祀的社会功能体现在对人的心理鼓舞方面。长期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神道教研究,多强调神道与日本国家、天皇之间的关系,强调神道维护天皇制的政治功能。其实除了政治功能以外,神道、特别是本文涉及的古代神道并不仅限于政治方面的功用,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等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神祇官是日本律令制时期的国家机构之一,主管祭祀事务。
②西田长男:《镇花祭一斑》上、中、下,《神道史研究》第15卷,1969年第2、3、4期。
③次田润:《祝词新讲》,明治书院1927年版,第352页。
④梅田义彦:《神道的思想》第2卷,雄山阁1974年版,第90页。
⑤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日本书纪》第1卷,小学馆1994年版,第272-274页。日本古代许多文献是用汉文体写成,其中很多文献中运用了一些日语词汇,文法和句式也受到当时日语影响,不是完全正确地道的古汉语,日本语言学界称之为“和式汉文”。笔者在引用时根据汉语语言规则进行必要的翻译和调整。
⑥关于神灵作祟,参照拙文《日本的灵魂作祟信仰》,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1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
⑦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古事记》,小学馆1997年版,第206-207页。
⑧《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载了很多神话,日本学术界统称为“记纪神话”。
⑨出云国,在今日本岛根县东部。
⑩黑板胜美主编:国史大系《律·令义解》,吉川弘文馆2004年版,第77页。
(11)黑板胜美主编:国史大系《律·令义解》,第77页。
(12)黑板胜美主编:国史大系《令集解前编》,吉川弘文馆2004年版,第196页。
(13)卜部是古代日本以占卜为职业的集团,律令制时期有一部分卜部在神祇官供职。
(14)冈田庄司:《平安时代的国家与祭祀》,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4年版,第634-635页。
(15)黑板胜美主编:国史大系《交替式·弘仁式·延喜式》,吉川弘文馆2004年版,第171页。
(16)次田润:《祝词新讲》,第99页。
(17)《倭名类聚抄》元和三年古活字版二十卷本,勉诚社1978年版,第12-13页。“衣也美乃加美”以及“於尔”是万叶假名,分别读作“ぇやみのかみ”(eyaminokami)和“ぉに”(oni)。
(18)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续日本纪》第2卷,岩波书店1990年版,第293页。
(19)刘熙:《释名·释天》,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9页。
(20)何晏、唐玄宗注:《论语注疏·孝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21)魏征撰:《隋书》第1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47页。
(22)李邕:《金谷园记》,原文曾传入日本,后来散失,镰仓时代成书的《年中行事秘抄》中受到其影响,并引用了其中部分字句。参照塙保己一编:《群书类丛》第6辑,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60年版,第595页。
(23)神道大系编纂会编:《神道大系》(朝仪祭祀编第1卷)、《仪式·内里式》,1980年版,第285页。
(24)此处引用的是郑玄在《礼记正义》中对于季春傩的注释,原文是“此难(傩),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引自《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64页。
(25)黑板胜美主编:国史大系《政事要略》,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10-215页。
(26)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续日本纪》第3卷,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280页。
(27)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续日本纪》第4卷,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430页。
(28)“畿内”原来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地理概念,古制把王城四周500里的地区称为畿内。日本把天皇居住的山城国及其周边的大和国、河内国、摄津国、和泉国称为畿内。
(29)黑板胜美主编:国史大系《交替式·弘仁式·延喜式》,第54页。山城国是今京都市一带,伊贺国是今三重县西部上野盆地一带。
(30)日本学界对于这两个祭祀中的边界观念论述较多,如和田萃:《夕占与道飨祭》,《日本学》1985年第5号。
(31)平田笃胤:《古史传》第6卷、《平田笃胤全集》第7卷,内外书籍出版社1931年版,第14页。
(32)黑板胜美主编:国史大系《本朝世纪》,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192页。
(33)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日本灵异记》,小学馆1995年版,第196-197页。
(34)关于“鬼”字的古代日语读音,目前学界通行的说法有もの(mono)、しこ(siko)、ぉに(oni)三种,但是笔者查阅《倭名类聚抄》发现,还有训读为“加美”(かみkami)、“太万”(たまtama),如“疟鬼”中的“鬼”训读为かみ,“穷鬼”则训读为“伊岐须太万”(ぃきすたまikisutama),即活着的人的灵魂。可见平安时代日本对于中国“鬼”字的理解是多种多样,分为ものかみ等不同的范畴。
(35)范晔撰:《后汉书》第3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22页。
(36)神道大系编纂会编:《神道大系》(朝仪祭祀编第1卷)、《仪式·内里式》,第285页。
(37)三宅和朗:《日本古代大傩仪式的形成》,《日本历史》1991年11月总第522期。
(38)笹生卫:《奈良、平安时代疫神观的诸形态》,二十二社研究会编:《平安时代的神社与祭祀》,国书刊行会1986年版,第390页。
转自《世界历史》(京)2010年2期第85~94页
责任编辑:刘悦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