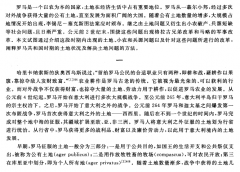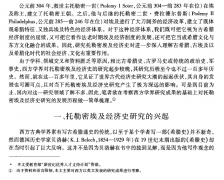试论拜占庭的拓殖运动
【英文标题】On the Immi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Byzantine
【作者简介】徐家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春 130024)
【内容提要】 7-9世纪拜占庭的农业拓殖运动,是中世纪世界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在实行军屯和民屯的政策方面,拜占庭继承了罗马共和到帝制时代的历史传统,但与罗马时期以开疆拓土为目标的外张性拓殖相比,拜占庭拓殖的主要目的是守护边疆、强化政府管理机制。拓殖政策的实行,使得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半岛上的“新来者”将其“蛮荒时代”的社会和生产结构方面的因素糅进拜占庭的社会生活当中,促进了中世纪东地中海各不同起源的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了一个堪称为“东方基督教文化圈”的东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形成。
【关 键 词】拜占庭/拓殖/东地中海文明共同体
7-9世纪间,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和扩张,原被誉为“罗马帝国大粮仓”的拜占庭属埃及沦陷于阿拉伯人之手,多瑙河流域也经常处于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外来民族的攻击和控制之下,农业发展的空间开始局限于黑海南岸的本都地区、小亚细亚、希腊—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等地区。但是,拜占庭人仍然坚持以“农业为本”①的传统国策,他们坚信:“农业和军事技术”是保全一个国家的重要依据②。由这一基点出发,帝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有条不紊地实行了强制性的移民(民屯)和军事拓殖(军屯)政策,以保证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使得拜占庭能够在经常处于新兴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南北夹击的困境下发展生产、强化边境治理,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奠定了10世纪拜占庭历史上之“辉煌时期”的基础。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东地中海区域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拜占庭东方基督教文明”这个大环境下的融合。
一 拜占庭拓殖活动的罗马传统
拜占庭的拓殖活动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至少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能找到与它相似的生产组织形式。罗马士兵、和平居民的开疆拓土活动与活跃于整个地中海—罗马世界的商贩们的贸易活动是随着罗马的不断对外扩张而步步延伸的: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不列颠岛、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地区、日耳曼尼亚、多瑙河南岸的潘诺尼亚,至巴尔干半岛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乃至埃及尼罗河流域、北非的努米底亚和利比亚地区,形成了以意大利半岛为圆心,以罗马军队和移民、商人的外向活动为半径向外辐射的“罗马化”(或曰“拉丁化”)运动。在所有移民区内,都很快地奠定了罗马移民役使当地土著居民的管理模式和罗马文明的统治地位,同时实现了民族融合。公元154年,一位被称为“诡辩家”的罗马人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在罗马城发表的著名演说《罗马献辞》中,非常自豪地称罗马帝国是一个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在开明的管理者或领导者英明治理下的、包括希腊、意大利和外省的“自治城邦的联合体”。在这里,没有作威作福的君主,也没有希腊人同野蛮人、土著人和异邦人之别,整个社会是和谐、平等的③。但他承认,罗马世界的平等不是绝对的,“上智者”和“下愚者”之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智者治人,愚者治于人的模式也始终存在。只不过,他所强调的上智者,并不仅局限于罗马人或拉丁人,而是指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各地区所有精英人士。这种态度,反映了罗马—地中海世界统一观念(orbis romanus)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
在罗马共和晚期至早期帝国时代一些政治家的积极推动下,这种外向型的“罗马化”和“都市化”运动发展颇为迅速。于是,在莱茵河流域、不列颠、西班牙、达尔马提亚和东地中海的希腊化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罗马名人命名的新建城市,如“图拉真堡”、“普洛提娜堡”、“马尔契亚堡”和“阿德里亚堡”等。有些城市,如科隆、美因兹、沃姆斯、科不林士、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等,“直到帝国历史的后期,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军营”④。另一方面,为了安置那些在罗马国家的军事扩张中付出青春和健康代价的退役军人,罗马人也在阿非利加、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建立了众多退役军人移居地,即所谓的“屯市”(colony)⑤,它们虽然只是被广阔农耕区域所包围的军人集聚区⑥,但却是罗马政府用以恢复被征服地区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组织形式,“……一个地区被征服以后,紧跟着的,便是开发农业、进行殖民、筑造道路、兴建港口等等事业,所以一般的结果,那被破坏地区的物质复兴,能迅速地完成”⑦。
除了军人之外,受到皇帝惠顾的平民和商人也有机会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安身立命。据记载,第三次布匿战争后,曾有6000名罗马公民(包括一些投机商人)在非洲获得地产,形成“一个非常有钱而又有势力的业主阶层,他们的世袭领地和大地产遍布全境”⑧。达契亚显然也有一批这样的罗马移民,他们是在图拉真皇帝征服之后陆续迁徙进入的。据称,当皇帝哈德良想放弃达契亚,把罗马军队撤回多瑙河南岸时,遭到了这些罗马移民的强烈反对,致使这一政策不能实行⑨。
为了保证罗马公民在行省中的数量优势,罗马统治者们在被征服地区实行了“掺沙子”的移民方式。如图拉真征服努米底亚及其邻近各省的土著居民部落之后,先将当地土著居民的全部土地没收,分别归入“皇产”⑩和私人地主名下,然后将失去土地的部落居民强行迁移到罗马人占领的其他地区,以补充罗马退役军人或皇产管理者所经营的各类田庄中劳动力的不足(11)。不久后,这类屯市很快获得了城市特权,在政府关注下建立了对当地青年公民进行军事训练的社团组织,使之成为罗马军队的后备力量。在这类屯市的外围农村,从事耕作的人群是大量的屯户(coloni,或译为佃户)(12),而不是奴隶(13)。
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特别是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确立了以军人为本的基本国策后,更多的军人或平民屯户出现在帝国已经征服或者是新征服的土地上,特别是皇庄和皇家的禁田(defensiones或defentiones)之上。塞维鲁重视多瑙河及叙利亚等地的农民,对他们的作战本领颇为赞赏,“竭力要在阿非利加创造一个类似的阶级”(14)。锡提菲斯地区出现的一些碑铭文件中,揭示了塞维鲁时期在上日耳曼尼亚、色雷斯、叙利亚、阿非利加、埃及等地安置移民的特点:他使农业居民(包括“蛮族”土著居民、士兵和罗马化的非拉丁居民,即“屯户”)集中居住于原本驻军的设防堡垒中,授予相应的自治权,使之承担维护边防的任务,在必要时则编入野战军上前线作战。这些屯市内的居民名义上是屯户,“其实是军事化的小地主”。于是,他们以这些碑铭文字表达对皇帝感恩戴德的情绪。他们所居住的农村,也成为“皇权的主要支柱”(15)。就这样,塞维鲁成功地实行了农民阶级的军事化,做到了藏兵于民,同时也有效地开发了边疆经济。后人注意到,4-6世纪以后,在叙利亚、埃及、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地区等军事“屯市”密布的农业区,其经济繁荣程度令世人瞩目(16)。
尽管,塞维鲁将罗马军队至少部分地“转变为一群定居的农民”这一政策的后果并不尽如人意(17),但其后人却并没有放弃这种政策。塞维鲁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222-235年在位),曾下诏将所征服的土地(包括土地上的奴隶和牲畜)分配给辅助部队的首领和士兵,而且规定,受地者须世世代代为帝国服兵役,他认为:“如果战争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土地,那么他们将会付出更大的热情……”(18)这种价值取向显然被中世纪的拜占庭所继承,于是,在斯拉夫人大量进入巴尔干半岛,阿拉伯人大批涌入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新的拓殖形式陆续出现在拜占庭帝国仍然控制着的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土地上。
二 7-9世纪拜占庭的拓殖运动
与罗马时期相似的是,拜占庭的拓殖活动也是先由军队开始,后推行于民间。
拜占庭军事拓殖运动的出现,可上溯到4世纪蛮族入侵时期(19)。当时,由于战事频繁、兵源缺乏,帝国开始在军队中大量使用蛮族人,境外一些骁勇善战的“蛮族”战士也“受到鼓励在帝国西部安家”(20),在不列颠、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兵役,其中有日耳曼人、阿兰人、萨尔马特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员,“帝国通常为这些移民提供家宅和税收总额的1/3”(21)。383年,因狄奥多西一世签署法令将西哥特人安置于色雷斯,受到一位宫廷诗人帕克塔斯·德雷帕尼乌斯的大加赞叹,他写道:“你收留了哥特人,为你的军队又增添了战士……并且为你的土地提供了农夫。”(22)后来,罗马军中的蛮族士兵数量更加扩大,甚至奴隶们也正式进入军队,狄奥多西的继承者霍诺留(395-423年在位)于406年颁布的诏书透露了这一信息,诏书强调:“奴隶们将为战争奉献他们自己……那些在军队服役士兵及盟邦和外国自由民的奴隶们……很显然……正在与其主人一起作战。”(23)
这些“与主人一起作战”的奴隶,并不一定终身为奴,一旦立了军功,就会很快获得自由,有些甚至能攀升高位,进入上层统治集团。此即被许多学者关注到的“拜占庭军队的蛮族化”或者反过来说,即“蛮族士兵的罗马化”进程,尽管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罗马化程度是非常浅的”(24)。狄奥多西一世时期,由于那些在他宫中“居于高位的日耳曼人”肆无忌惮地骚扰百姓,曾引起过萨洛尼卡市民的反抗。但皇帝毫不留情地镇压了敢于反抗的民众,“妇孺皆不予赦免”(25)。5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庭的阿兰人军事首领阿斯帕尔居然能够执掌朝政,甚至经他一人之手选任了两位皇帝(26)。出身于小亚细亚陶鲁斯山区伊苏里亚部落的芝诺(474-491年在位)则在拜占庭皇帝对抗蛮族势力的斗争中,通过婚姻与政治联盟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皇权(27)。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476年在罗马古都颠覆了罗慕洛·奥古斯都统治的奥多阿克也是权倾朝野的西哥特人军事将领。
拜占庭帝国军队中哥特——蛮族人势力的崛起曾经引起元老贵族势力的极大担忧,5世纪著名元老派代表希奈修斯致狄奥多西之子、拜占庭皇帝阿卡第的谏议书“论皇权”就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忧患意识。该演说特别回顾了狄奥多西皇帝赐予蛮族士兵土地、同盟者地位和政治权力的慷慨之举,认为“罗马”皇帝对于蛮族异己势力的特别恩宠会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础,他还痛心疾首地请求皇帝下手“清理军队”,以免“杂种发芽”危及良种(28)。
然而,少数元老贵族的呼声并不能阻止拜占庭军队的蛮族化进程,而且,在早期拜占庭,军队的蛮族化与士兵的农民化几乎是同步的。“当军队逐渐整合成社会的非军事机构,大部分士兵成为士兵—农民,同时有的成为士兵—镇民的时候,国内的人口便逐渐军事化了。”(29)这种“军事化”的人口构成拜占庭皇帝手中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野战军,使得6世纪的皇帝查士丁尼能够得心应手地借助这支军队(30)和他手下的优秀将领贝利撒留、纳尔泽斯打赢了对北非汪达尔人、意大利东哥特人和西班牙西哥特人蛮族政权的长期战争,基本实现了其“光复帝国”的宏愿。随后,他任命的北非驻军将领借鉴了古罗马时期建立军事性“屯市”的拓殖方式,在北非占领区实行了军事拓殖运动,使边防军人“农民化”,艰苦地、但有效地阻止了非洲土著摩尔人对拜占庭统治区的干扰,稳定了“罗马人”(31)的统治。莫里斯皇帝(582-602年在位)统治时期,更进一步在北非的迦太基和意大利拉温那两个新征服地实行了军政合一的“总督制”,并使戍边军人在休战时期开发边疆土地,发展农业经济、保障军队供给的拓殖模式成为边疆管理的特殊模式(32)。
希拉克略王朝时期(610-711年),由于东方边境上拜占庭夙宿敌波斯的长期压力和7世纪中期以后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对外的军事行动和有效的边境防御成为维护拜占庭帝国之生存的重中之重。希拉克略采用了向地方教会借贷的非常手段,取得了对波斯战争的胜利(329年)(33),但又不得不立即面对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造成的近东和小亚细亚地区大片无人耕种的边疆荒野又被新兴阿拉伯人夺去的威胁。于是,以军区制的建立为标志的军事移民和以安顿巴尔干半岛新来者斯拉夫人为目标的农业移民就成为拜占庭政府解决上述难题的重要政策性措施。
在军区制度下,政府将分散于帝国各边界要塞之地和多瑙河岸的驻军划分为数个军团戍守区,由军团将军操纵当地最高的军事、行政、司法和税收权力,选任文职官员管理非军事事务。那些无人耕作的土地则按照罗马时代的传统,依军事编制逐级分给官兵,使他们亦军亦农,在战后的和平期间开发边境地区荒芜的土地资源,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补充军队的基本给养。同时要求他们在对敌战争需要时随时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家园(34)。
关于军区制建立的原因和大体时间范围,学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20世纪早期的一些历史学家如瓦西列夫和奥斯特洛戈尔斯基通常强调,军区制建立于希拉克略对波斯战争之后,即7世纪30-40年代间(35)。瓦西列夫在援引了库拉科夫斯基和路易·布莱耶尔的观点后,指出在希拉克略结束了波斯战争、“改组亚美尼亚政府时,没有任命文职行政官员,掌权者完全是军方人士”(36)。当代美国拜占庭史家瓦伦·特利德哥尔德(Warren Treadgold)则认为,拜占庭以推行农业拓殖为手段的军区制出现的时间,应该不早于康斯坦斯皇帝(641-668年在位)统治后期(37)。他还特别强调,拜占庭之所以实行军区制,是由于7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庭国家除了荒芜无主的土地资源外,已经没有能力支付士兵的薪饷。他强调,近年来,考古学家们在西亚一些地区发现的铅制印章能够证实:7世纪的拜占庭政府经常征收实物贡赋以解决士兵的武器和军装供给;另一方面,在安纳托利亚地区鲜有7世纪中期以后帝国发行的钱币出土,这多少说明了对波斯战争之后,近东地区商品经济衰落的事实(38),也多少揭示了在7-9世纪军区制的实行的特别必要性。
除了实行军屯政策之外,为了缓和边境地区的政治、宗教、民族矛盾,7-9世纪的拜占庭皇帝们还经常实行强制性移民的“民屯”政策。希拉克略皇帝统治时期,“采取了一项对于巴尔干半岛前途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步骤”(39),他将喀尔巴阡山麓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移至亚得里亚海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和伊利里亚地区,让他们耕种当年罗马人和希腊居民所放弃的土地。另外一些蛮族群体,如哥特人,潘诺尼亚的赫琉来人和塞加西亚人、阿拉伯人、埃及人、波斯战俘、突厥血统的阿瓦尔人等,也被分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其中,阿瓦尔人被安置在美塞尼亚附近的那瓦里诺;保加利亚人被安置在亚克兴海周围;另有1.5万名突厥人被安置在东马其顿地区;其他民族被安置在奥赫利德湖(40)四周。在被强制移民的拓殖者中,斯拉夫人占绝大多数。
希拉克略王朝的末代皇帝查士丁尼二世(41)(685-695年,705-711年在位)时期,政府推行的强制性迁徙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据记载,他在东马其顿地区和斯特莱蒙河谷一次性地安置了斯拉夫人战俘7万名之众(42),另将8万名斯拉夫人迁徙到小亚细亚的奥普西奇翁(Opsikion)军区(43),其中有3万人是以军队调动形式迁徙到位的。这些斯拉夫人被安置下来之后,很快接受了东正教和希腊人的语言文化,成为拜占庭农村劳动者的主力,其原始的野蛮性也渐渐被希腊人所同化。调到奥普西奇翁军区的斯拉夫人参与了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但因其在战争中背叛了皇帝查士丁尼二世,遭到可怕的屠杀(44)。著名中世纪考古学者B.S.潘切恩科(Panchenko)发现了当年奥普西奇翁军区比西尼亚省斯拉夫人军事移居地的一枚印章,他认为这枚印章是“斯拉夫部落历史的新的片段”,它“在大迁徙的迷雾中透出了一线光明”(45)。
在拜占庭对阿拉伯的长期战争中,迫于阿拉伯人的压力,查士丁尼二世还将叙利亚前线的边境居民——马尔代特人强行迁徙到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伯罗奔尼撒和伊庇鲁斯、塞萨利等地定居。这批马尔代特人原来是居于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叙利亚边境之间的自由边民,因其忠实于拜占庭皇帝,在边境上形成阻止阿拉伯人渗透的重要“隔离带”,曾一度成为阿拉伯人的心腹之患(46)。查士丁尼二世的这一移民行为,削弱了拜占庭边防,显然有利于阿拉伯人对拜占庭边境的骚扰和侵犯。
伊苏里亚王朝(717-847年)时期,政府强制性移民的主要目标是活跃于小亚细亚的摩尼教徒和保罗派(47)、雅各派教徒,他们被政府强行迁徙到色雷斯和希腊半岛。拜占庭皇帝以为,这种做法既可以缓和这批异端教徒对于小亚细亚各省的宗教和政治稳定造成的影响,也可以利用这些民族英勇善战的特征抵抗拜占庭北疆最具威慑力的保加利亚人,显然是“一箭双雕”之举。另一方面,自多瑙河沿岸南下,自行进入荒芜空虚地区的斯拉夫人自由移民也往往成为政府政策的补充。因此,至8世纪早期,斯拉夫人已经分散于希腊半岛各处。迪拉基乌姆(今都拉索——译者)和雅典城均有斯拉夫人出现(48)。利奥三世时代,一位去耶路撒冷圣地朝觐的西方人在途经伯罗奔尼撒城市蒙内姆巴西亚时,认为这座城市“处于斯拉夫人的土地上”(49)。746-747年,源自于意大利的大瘟疫使首都君士坦丁堡人口迅速减少,政府从爱琴海诸岛和希腊腹地移民到首都周围以保持首都的繁荣。于是斯拉夫人乘虚而入,充实了希腊半岛上那些荒无人烟的“真空”地带。女皇伊琳娜被迫派出专门部队去对付伯罗奔尼撒半岛、萨洛尼卡和希腊腹地那些不驯服的斯拉夫移民(50)。“紫衣家族的”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作《论军区》中强调说,“当鼠疫在整个世界蔓延时,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变得斯拉夫化和野蛮化了”(51)。与此同时,迁至小亚细亚的斯拉夫人数量也迅速增加,到762年,迁至小亚细亚的斯拉夫人数量已达20.2万人之多。
西方著名经济史专家齐波拉在其《欧洲经济史》中列出了东地中海地区人口公元500-1000年的人口估计数字简表(52),从中明显可见这一地区人口增长的幅度:
东地中海地区公元500-1000年的人口估计数字简表(单位:百万人)地区 500年 650年 1000年
希腊和巴尔干 5 3 5
意大利 4 2.5 5
上一篇:试论波斯帝国的行省与总督
下一篇:日本遣外使与文明载体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