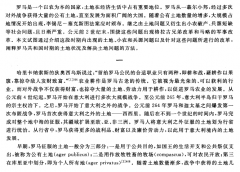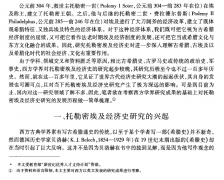塔西佗史学初探
【英文标题】 On Tacitus' Historiography
【作者简介】褚新国,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褚新国,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
【内容提要】 作为帝国早期罗马社会的现实产物,塔西佗史学具有深远宽泛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浓烈复杂的政治伦理意蕴:政治观对其史学创作产生了深重影响,撰述旨趣则与其现实隐忧息息相关。在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意义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严格的社会批判精神,并进而形塑了其凝重简练的历史叙事风格。塔西佗史学集中体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某些共性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历史。
Tacitus' historiography has a far-reaching implication of society and history, especially a profound meaning of political ethics. Tacitus social political view influences his history writing profoundly. In the sense of the historical view on ethic and strong intention of morals, Tacitus' historiography incarnates the hard and fast animadversion on his time, and shapes his condense historical narrative. Tacitus' historiography displays well som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cident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in its own developing course, and influences the whole Occident in history to a certain extent.
【关 键 词】塔西佗史学/道德史观/道德目的/西方古典史学Tacitus' historiography/historical view on ethic/ethic intention/the Occident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6~118年)是罗马帝国早期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和文学修辞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人们总是热衷于将一个复杂矛盾的塔西佗打上林林总总的标签符号:或持身守正言行如一的道德哲人,或共和政治的狂热崇拜者,或鼓吹罗马至上的帝国主义者,或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或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谎言家、反基督教分子、王权掘墓人,等等。较之其他拉丁史家,塔西佗总是享有世间最多的赞誉抑或非难,这一点即使从其作品命运多舛的传播流变史中亦可略见一斑。自文艺复兴时代被重新发现之后,他的作品就再现生机并对整个欧美世界产生深远广泛的历史影响:14至15世纪,人们阅读塔西佗的兴趣开始恢复并逐渐升温;在16世纪的西方,小普林尼的预言终于获得历史首肯性的检验。自上世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有关拉丁史家尤其是塔西佗的研究开始重新蓬勃兴起(他在19世纪曾经一度“失宠”):刚刚走出战争阴影的人们对心理学的痴迷和热衷,以及对形形色色专制主义的反感和抗拒等诸多现实因素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 鉴于学界目前尚有许多分歧有待进一步廓清厘定,本文试图对之进行一番疏浅的解读。在我们看来,这对于深入发掘塔西佗史学的丰富意蕴,辨明西方古典史学演进过程中的某些共性特征,无疑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囿于学识等局限,拙文或多有疏漏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为是。
一
塔西佗史学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进入帝制以来,面对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实践问题,历史学家及其研究工作正在日益深刻地参与和推动罗马社会的创新过程,并成为整个社会实践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写什么”、“怎样写”以及“为什么写”的问题就突出摆在塔西佗面前。事实上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塔西佗对诸如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复杂性和规律性、历史发展的趋向动力、罗马与周边蛮族的关系以及重大历史人事评价的原则方法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对诸如撰史目的、史学职能、表达风格、史家主体修养、史书编撰方法以及史料处涉等一系列重大史学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论及且在许多方面不乏真知灼见。一方面这是塔西佗对前代史家史学创作以及他们撰述理念总结概括的理论结晶,另一方面更是他面对罗马国家社会现实问题,试图通过史学这一批判武器而寻求挽救时弊方法的理论探索。如果说社会危机和时代思潮在根本意义上直接催生了塔西佗史学,那么,经世致用的撰史目的在客观上也相应要求其不能不对上述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予以思考和回答。尤其是考虑到不同政体的统治实质,因地制宜地研究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性情心理及其意愿要求,实乃史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分内之事——譬如在平民掌权的情况下,就必须研究“群众的性格和驾驭他们的办法”。尽管塔西佗从不曾真正消解过对帝制专制独裁统治的强烈憎恶和坚决抵制,但帝制代替共和且逐渐巩固确立下来却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作为一个以国家兴亡民族荣辱为己任的清醒理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无法拒绝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至少在刚刚身临帝制统治的现实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缺乏实际统治经验而在黑暗中踯躅摸索的最高统治者,还是因张皇失措而手忙脚乱的普通民众,都迫切需要一些能够安身立命且行之有效的“实惠的东西”。这是时代对史学应具备的社会功能的迫切要求,从中也能折射出史学与政治、历史与现实之间紧要的动态关联。作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塔西佗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开展撰述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其史学实践的前瞻性和进步性。
在此意义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其深沉远大的历史意识。但凡一个优秀史学家,促使其关注并研究历史的重要思想基础,即在于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严重关切和以天下兴亡社稷荣辱为己任的忧患意识。而且在历史大转折大变乱时期,在国家民族面对多种政治文化抉择和生死存亡之际,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会更深沉、更痛切、更显著。[1](P1) 作为古代西方史学中一个重要的优良传统,重视从历史的兴衰递变中获得经邦济世的启迪,同样也是塔西佗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公元1世纪前期的罗马政局动荡社会混乱, 走马灯似上台的政治强人用屠刀和鲜血埋葬了共和国确立了帝制统治。面对如此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塔西佗心中强烈的忧患意识追拥着他对历史进行冷静思考,从而迸发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意识。正是出于对撰史崇高社会职能及其与现实政治生活微妙关系的深刻洞悉,塔西佗坚决批判趋炎附势隐恶溢美的不良“学风”,并积极捍卫亲身践行秉笔直书善恶无隐的撰史主张。所有这一切,都鲜明地表现了史家善于从历史宝库中发掘材料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意识。
任何史家的撰述旨趣都不是孤立无援的存在,而是与其有关社会现实的根本看法彼此呼应的,因为史学思想归根结底是史家在反思历史与当下现实过程中的一种思想意识层面上的积累和沉淀。[2](p132~136) 史学与现实社会之间复杂而紧要的关联性,在社会转型之际体现得尤为显明。在此意义上,塔西佗史学正是公元1至2世纪罗马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彼此矛盾统一的历史产物。[3](p778,P819) 倘如是,塔西佗史学创作的历史意蕴同样可在此宏观视域下获得理解和体认。为此我们强调两个基本的因素——个人主观的和时代历史的。即塔西佗个人的先天禀赋、后天主观努力及其所处的独特的历史境遇,包括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思想意识形态、罗马文(史)学创作及其相应的书写传统等等的作用。凡此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因素聚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终于使得塔西佗能够以政治家、文学家、道德家和历史学家的“复合型”多重身份撰史。这就是塔西佗,一个集政治家的深刻、历史学家的敏锐、文学家的材质和道德家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于一身的史学大家,一个通过生花妙笔深刻彰显其人、其世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旷世奇才!当然,深入理解和阐释塔西佗独具精妙意蕴的表达风格及其撰史理念,远非笔者学力所能胜任。但我们或许要问:为什么这一切恰恰是发生在新旧社会体制的全面转型之际、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变革时期、在拉丁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正是罗马批判(或暴露)史学大放异彩的全盛时期呢?
二
社会政治观对塔西佗的史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政治思想史,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为修昔底德所奠立。[4](p54) 在此意义上,道德问题是塔西佗认识和把握罗马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全部而惟一的关键所在。通过对罗马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反思,塔西佗不得不认真回答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当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导致国家问题丛生罪恶遍野的根源何在?个体生命与国家民族究竟如何获得救赎之道?德性生活及其实现路径究竟如何可能的?凭借一个成熟政治家和卓越历史学家的敏锐视界,塔西佗洞察出罗马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动:至少,古罗马人的无限风光、共和衰亡帝制勃兴、当下的不幸与罪恶以及拯救国家民族的“济世良方”等所有的一切,只有古罗马道德遗风的恢复才能提供并承载所有问题解决的惟一期待和终极答案。事实上,塔西佗从不曾去关注任何一个与国家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毫不相干的“纯粹”道德问题,而其全部史学实践惟一的叙事主题即在于兹。塔西佗所谓的“德性生活”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上予以体认:在积极的社会政治层面,它是拯救国家惟一有效的现实路径,每一个普通公民之与德性生活的践行即意味着整个帝国命运的希望与未来;在消极的个人生活层面,即使由于恶人当道,好人不能征服或控制一个邪恶的世界,对德性生活的践行仍然可以确保生命个体免于种种罪恶的玷污。然而在罗马人普遍道德沦丧的当下,这种希望与未来又渺茫得近乎乌有之乡。在此意义上,我们或可充分理解塔西佗道德史观视域下的撰述旨趣及其撕心裂肺般的伤痛。
在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意义和基础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其严格的社会批判精神。罗马观构成塔西佗主观上批判意识的直接前提,构成其客观上从事史学撰述的一个根本动因。尽管单从道德视角考察社会历史或许有褊狭,但塔西佗毕竟注意到并强调了帝国社会阴暗腐朽的一面,其对罗马各种矛盾危机的揭露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真实地再现了历史。[5](p357) 尤其是政治昏乱与道德败坏的紧密结合,有利于史家将道德批判上升至社会政治批判的层面,从而大大深化了其道德叙事的社会政治意义。譬如,塔西佗敏锐地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对罗马世风日下的深刻影响,并试图以此来发掘国家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经济动因。囿于种种局限,塔西佗不可能懂得历史变革中经济因素的决定性意义,但这仍然体现了其深刻的历史洞见和敏锐的历史视野。更为可贵的是,塔西佗从道德史观出发将人的道德实践与社会经济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如罗马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以及希腊人等)社会物质生活与道德状况彼此间微妙关系的探讨,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内涵,从而为其道德批判注入了新的社会历史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破除了罗马史家传统道德史观的空洞性,从而体现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由是,塔西佗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与历史事实、历史进程及其运演规则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为其道德史观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现实批判基础。在此意义上,道德叙事彰显了史家将社会批判精神融入史学撰述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需要强调的是,惨烈的严酷现实与强烈的批判精神深刻影响和形塑了塔西佗的历史叙事风格。塔西佗史学总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辛酸与无奈,一种抗争与忧愤。在塔西佗看来,似乎只有痛苦才是崇高的,因为在人类所有的历史与现实中惟有它最为深刻,而且只有表达或者表现出史家痛苦的作品,才是真实有力而又有益的。种种残酷的社会政治现实促使塔西佗坚信:帝制政治是导致罗马充满灾难与不幸的渊薮,暴君及其暴政罪不容恕。在此意义上,通过“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与“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塔西佗力图传达出一种关于当下罗马不堪回首不堪入目令人心碎的表情与声音。通过凝重简练含蓄深沉但又充溢丰沛感情色彩的语言,他从容不迫掷地有声地展现出近一个世纪罗马与罗马人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及其繁复丰富的性格深度。其间,通过纪录每个罗马人并不遥远的现实和记忆,塔西佗言说个人的不幸、国家和民族的伤痛及时代的苦难与罪恶。在他的笔下,有死亡、阴谋、杀戮、背叛、投机、征兆、饥馑、天灾等,所有这一切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上演,这样的内容充溢于作品的每一个字缝,从而以令人窒息的触目惊心的容量和密度描绘了一幅“充满了灾难历史”的图画。于是史家抚古思今,却只为国家惨不忍睹的寂寥景况而忧心忡忡、痛心疾首。惟有将愤懑与憎恶投射于阴森恐怖的景象之中,积淤于胸的心愤难平或者可得以释放舒缓些许。通读其作品我们分明可以感知:遍及于字里行间浓郁的愤懑悲怆和压抑沉重的气息扑面而来,再辅之以声情并茂细致入微的性格心理刻画,从而让作者读者共同见证了一个令人伤心欲绝的时代。② 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说明,为什么塔西佗的作品基调以阴郁为主色——哀生民之多艰,涕国家之多舛兮!尽管撒路斯提乌斯、李维以及苏维托尼乌斯、狄奥等史家也都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抨击罗马政治与道德领域的昏乱,但似乎惟有塔西佗将之进一步上升到一种深沉的近乎绝望的高度。倘若假以时日再书写涅尔瓦与图拉真时代的历史,他是否愿意写出与《历史》、《编年史》迥然有异的东西来呢?塔西佗似乎不得不将其视野中的那个世界及其所理解的那个时代整个地置放于萧瑟灰暗的景象当中——惟有在“充满了灾难的历史”以及诸如此类线条的“真实”呈示中,或可寻求些许关于救赎国家及民族前途命运的力量和福音罢。③
三
作为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修昔底德、波利比阿、撒路斯提乌斯等优秀史家的撰述实践,为西方古典政治军事史学范型的创立和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但他们又大多仅停留于经验的层面而未上升至理论的高度,更多的打上了书写者个人风格的烙印。就此而言,前代史家能够为塔西佗所承扬的直接性经验似乎并不太多,至少从文本讯息来看不甚明显。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关塔西佗史学的认知能否为进一步理解拉丁乃至整个西方古典史学提供某些启示性借鉴?或倘若以之为个案,它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更为深层次性的问题元素?考虑到塔西佗史学之与西方古典史学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地位和影响,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塔西佗史学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其作为一位天才文学家的材质——实际上,这也正是其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竭力推崇或肆意诋毁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倘若在原生形态的意义上考虑到罗马文学与史学之间微妙的共存关联,类似的问题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在西方史学近代化和专业化以前,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并非十分明确严格,而更多的往往是彼此间呈现出一种复杂微妙难分难舍的“胶着状态”。诚如论者指出的,对于罗马这样一个“其天性是眷恋过去”[6](p20) 的民族而言,“研究拉丁文学主要是为了理解罗马的历史”。[6](p1) 事实上,包含源自真实人物实例的“历史和道德哲学”,素来是罗马人“最感兴趣的文学和思想的分支”。[6](p91~92) “如此一来,其道德化和教化特征强烈,文学的目的在于教化——这就不足为怪了”。[6](p125) 同样不可否认,古今中外但凡大史家往往追求作品的艺术审美性,拉丁史家亦不例外。考虑到特殊的多重写作身份及其写作背景、撰史目的等,史家赋予作品一定的文学性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达方法的问题,这在古典政治军事史家及其史学实践当中可以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诚如论者所强调的,自伽图以降,“探索有效的文学表达方式”已经成为罗马史学显著的“标志性”特色之一。而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在于“罗马人认为历史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批判科学”。[7](p93) 因此以“清晰而有趣的文体进行叙述是历史的目的”,而且它已经构成罗马史学“不可或缺”的特点。[7](p108) 倘如是,这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拉丁史家的作品大多数可以被视作经典性的文学散文来读:或如李维之华美丰赡、叙事流畅,或如恺撒之清澈如水、朴实自然,或如撒路斯提乌斯和塔西佗之凝练含蓄、辛辣尖刻。尽管这种特色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拉丁史学创作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众所周知,基于道德成败的立场和视角来考察罗马历史与当下现实,强调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是非优劣功过得失的道德批判,是许多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罗马史家从事历史创作基本的叙事主题。在他们看来,罗马民族精神的践行与共和国的胜利、国家的政治腐败与道德沦丧之间是互为因果条件的。从老伽图到撒路斯提乌斯,从李维到阿米安,皆大致遵从了相同或相近的史学理念。就本案而言,古罗马淳朴的道德风尚同样是塔西佗观照令人隐忧作痛的罗马现实社会,并进而评断其是非功过成败得失的最基本的历史价值参照物。而且,这一思想特质我们同样可以在与其大约同时代的苏维托尼乌斯、塞内加、爱比克泰德、普鲁塔克、尤文纳尔等人的学术实践中充分地领略得到。譬如在尤文纳尔看来,“我们的罪恶已达绝顶,子孙后代永无超过可能”。在此意义上,“不幸尤维纳利斯也有塔西佗的作风,一个是用尖刻的笔法描写帝王和元老,一个是以怨言来讽咏男女”。“他的道德尺度对美好的过去很有偏见和误解,不过不失其崇高与正确。用那种无情无礼的道德标准,我们可以随时控诉任何时代”。相比之下,塞内加对于这种不满知之甚详,“我们的祖先从前不满,我们现在不满,我们的子孙也要对道德败坏、恶人当权、人们陷入罪恶、人类情形每况愈下等等现象不满”。[5](p361~362) 或者也可以说,当他们共同遭遇同一个现实世界分享同一种思想特质(譬如斯多噶主义等),并且不约而同地通过学术实践痛斥时代堕落、哀叹不幸与灾难的时候,彼此间出现一些具有共通性的学术指向和论题旨趣似乎又是情有可原而绝非偶然的。当然不可否认,塔西佗之与“他们”的差异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较之于李维对奠基人以及战场上喋血英烈的深情推许,塔西佗则更为欣赏政治斗争舞台上高尚人士的道德壮举,尤其是那些为捍卫共和政治理念和传统道德操守而从容赴难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塔西佗宣扬史学“惩恶扬善”的训诫功能但却绝不裹足于此,而是赋予传统的道德叙事以更为深沉凝重的社会历史内涵:他回避了先前编年史家肤浅的道德说教,也远远超越了李维等盲目的爱国热情;而认为在君主独裁专制体制下,政治美德较之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壮举更值得大书特书,其个体的兴衰荣辱也就等同于整个国家民族的沉浮悲欢。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塔西佗承扬了罗马传统的道德史学,并将其发展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境地。④
不可否认,强调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撰史传统发端于希腊史学而至罗马史学得以进一步承扬。尽管与之相比希腊史学在这方面似乎并不十分鲜明突出,但这绝对无法消弭、掩盖其强烈的道德性征。这一点即使是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例,也可以获得充分说明。诚如论者所强调的,希罗多德“好像无动于衷地记述了恶人善终、好人受罪的事实”,然而他绝不是要像人们所批判的那样“无视一切道德准则”,[8](出版说明·Pii) 相反正是崇高的撰述目的促使其“成为一位道德家”。[7](p34) 类似的思想旨趣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贤哲苏格拉底——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共同致力于对一种所谓“知识”的追求,即一种“有关人事的知识,特别是有关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观念的知识”。[9](p62) 在某种意义上,从大量似乎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中发掘隐与其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进而以具体的历史实例为世人提供道德教诲,几乎构成了古希腊史学重要甚或主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罗马史家对希腊史学书写传统的发扬光大更多体现在,他们往往在赋予作品更为深刻、凝重的政治伦理意蕴的基础上,突出彰显史学的实用化性征。这在塔西佗史学中获得了更为集中的体现。倘如是,在后续的拉丁史家那里,我们似乎很难再看到与古希腊前辈迥然有异的东西。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许多出色的史家在同样甚或类似的路径上踯躅而行——无论是撒路斯提乌斯抑或是李维,总是偏向于通过载录“阴谋”或“战事”为世人提供意味深长言词切切的道德教益。在塔西佗史学当中,我们更是可以完整而清晰地感知:诸如“人性”、“天命”等命题范畴究竟是如何在“惩恶扬善”的宏大目标下,通过史家的生花妙笔延展论说而直至最终得以有效实现的——尤其是,对诸如此类命题阐发的逻辑致思理路竟然如此惊人的集中而又具有不谋而合的“一致性”。
事实上就整体而言,西方古典史学的许多优点或缺点莫不与其道德史观及其道德目的息息相关。不可否认,许多古代史家具有浓烈道德色彩的史学实践往往会在不同程度上削弱史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一方面,文献史料的保存考订非其所长更非其所愿;另一方面囿于强烈的情感色彩,对历史人事的褒贬评断难免存有一定的偏见错误,等等。塔西佗史学同样在不同程度上集中反映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某些主要缺陷:譬如政治与史学的关系日益紧要化,国家政治生活进一步通过多种路径渗入历史撰述领域;譬如囿于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过多地渗入史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评判;譬如道德史观发挥极致,主宰了对客观史实的收集与解释;譬如片面夸大行为者罪恶或良善动机之与史事决定性的影响;譬如忽视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等深层次背景因素,撰史视野过于狭促,等等。总之,塔西佗史学不乏局部突破之处并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客观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但某种意义上又似乎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与正确回应,缺乏对无限丰富复杂的时代历史的多维揭示和全景考察。正惟如此,塔西佗史学遭到部分学者的强烈质疑和批判。譬如在柯林武德看来,“他仿效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的狭隘观点而不汲取他们的优点;他被罗马事件的历史迷住了,却忽略了帝国,或者只是通过足不出户的罗马人的眼光的折射来观察帝国;而他关于这些纯粹罗马事物的观点也是极端狭隘的”。[9](p75~76)
毋庸置疑,史学思想与实际客观历史进程总是存有内在逻辑性的一致。倘如是我们或许就不得不承认,古典诸史家在诸如逻辑致思理路、考察视角、论题内容等许多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其所同样作为古典奴隶制时代人们在诸如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某些共同共通性的具体遭际,以及基于其上的历史继承性与连续性密不可分。譬如之所以要以政治军事事件作为撰史的主要题材,首先主要或在于他们往往不得不大量地遭遇它们——不同民族、国家、政党之间开展的一系列规模烈度大小不一的斗争,而且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现实,恰恰正是这些斗争在当时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历史面相。在此意义上,作为行为主体的各个当事者的性格、命运、德行和活动动机以及诸如此类的物事范畴等,则往往无一例外地构成史家思考的全部论题或者论题的主要方面。许多杰出史家具体的史学实践充分表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他们往往不得不如此而为——就本质而言,他们总是要被这些发生于周遭的现实事件及其历史认识能力水平等事先即规定了的:包括什么才能够成为问题、怎样获得问题的圆满解决以及观察的视角和叙事的模式,等等。事实上,诸如人性论、天命论及英雄史观等命题,是西方古典史家领有强烈道德性征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展开实践的基本内容。上述指认几乎涵纳了始从古希腊直至罗马帝国晚期阿米安等优秀史家的史学实践,伴随并贯穿着西方古典史学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历史嬗变全过程,而塔西佗及其史学实践则是西方古典史学发展史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和集中折光!倘如是,我们是否可以说,塔西佗史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认识整个西方古典史学提供某种参照物性的考论范本?
目前学界一般倾向于同意:尽管一直身负众议但在晚近以来的数个世纪中,塔西佗所赋予笔下历史人事深刻的性格心理刻画、敏锐的政治分析、道德教谕及其出神入化的艺术魅力,一直强烈地吸引着老练的读者,甚或“很少有读者会对其惊世骇俗、醒世通言般的文体内容无动于衷”。[10](p98) 尤其是在人类近代历史上,从文艺复兴直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几乎毫无例外地一致认同塔西佗在形塑西方智性文明传统过程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11](p72~74) 就政治层面而言,作为专制暴君毫不妥协的敌人,塔西佗曾深深地吸引了蒙田、约翰·弥尔顿、约翰·亚当斯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大批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与此同时却也深深地刺痛了英国的詹姆斯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以及法国的拿破仑等大独裁者。而且,《历史》和《编年史》当中的许多卷章无论开头抑或结尾都更像是一个首尾兼顾的情节完整的戏剧,因此被后人广泛地改编成为剧本并搬上戏剧舞台和荧屏。诚如论者所强调的,“在同代人当中的卓尔不群也许是塔西佗时至今日仍然强烈吸引我们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独特的才智使之区别于其他拉丁史家”,因此漠视塔西佗也许会使实际情况变得更糟——毕竟,“他能够为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流派提供教条,为人性的每一个相位提供教益。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获取适宜于己的座右铭和行动准则。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阶段,在任何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人们都可以从中为其价值理念寻找到适宜的利益代言人”。⑤ 总之,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塔西佗及其作品已经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而且必将会在同样意义上对后世产生历久弥新的意义和影响!
收稿日期 2005—11—21
注释:
① 二战后西方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如下论著:B. Walker, The Annals of Tacitus: A Study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2; Clarence W. Mendell, Tacitus: The Man and his Work.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Ronald Syme, Tacitu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Donald R. Dudley, The World of Tacitu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8; J. Ginsburg, Tradition and Theme in the Annals of Tacitus. New York: Arno Press, 1981; Ronald Martin, Tacitus. London: Batsfod, 1981; Ronald Mellor, Tacitu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R. Ash, Ordering Anarchy: Armies and Leaders in Tacitus' Histor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E. O' Gorman, Irony and Misreading in the Annals of Tacitu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就整体而言,国内相关研究立论较为浅显,视野不够开阔,且许多论见属于定论性认知。囿于篇幅,兹不赘述。
② 帕拉托(Ettore Paratore, Tacito, Milan: 1951)拒绝承认塔西佗社会政治观在其所有作品中存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沃克则认为塔西佗很早即已逐渐认识到政治剧变之与罗马社会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编年史》体现并确证着其最终的持久的帝制观,即政治自由以及元老贵族有尊严地过活之可能性的丧失殆尽(参看B. Walker, The Annals of Tacitus: A Study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③ 在结语当中, 阿什着重探讨了《历史》和《编年史》为什么如其所愿般地结束,即正当“集体性的暴政危险烟消云散之际,叙事戛然而止”(参看R. Ash, Ordering Anarchy: Armies and Leaders in Tacitus' Histories, p168);高曼则强调了理解塔西佗在选材上的独具匠心,“自相矛盾的是,涅尔瓦和图拉真的统治使得反讽性的表达成为不可能……所以当论及二君统治之时,塔西佗格格不入而又粗鲁的声音也就理应沉寂下来了”(参看E. O' Gorman, Irony and Misreading in the Annals of Tacitus, p181)。
④ 参看B. Walker, The Annals of Tacitus: A Study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74,p156~157; R. H. Martin,“Tacitus and his Predecessors”,in T.A.Dorey(ed.),Tacitus(London:Routledge,1969),p117~47。
⑤ 在《塔西佗》最后一章(cf.Chap.11),马丁言简意赅地概述了塔西佗作品之于后世的传播情况。其中,论者着重强调了塔西佗观点对于16、17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的孕育催化之功——尤其是在充斥了战争、革命和专制的当下,我们对塔西佗及其作品的兴趣理应复兴。(比较参看:T. J. Luce, A. J. Woodman(edd.),Tacitus and the Tacitean Tradition, p.217; Clarence W. Mendell, Tacitus:The Man and his Work, Chap.12—19.)
上一篇:日本江户时代商家雇佣制度的合理性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