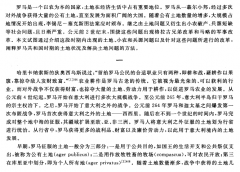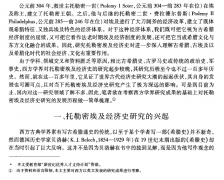论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英文标题】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tolemaic Egyptian Kingship with the Religious Authorities
【作者简介】郭子林,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 托勒密王朝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法老埃及的王权与神权之间从来就不是和谐统一的,始终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托勒密王朝,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有效地控制了神权。这主要是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借鉴了法老埃及的经验,采取了有利于王权的政治、经济政策,等级和阶级关系决定了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文化背景也使托勒密国王从意识深处拒绝给予宗教和祭司各种权力。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也正是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本土埃及人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 键 词】托勒密王朝/王权/神权
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前30年)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①西方学界自20世纪初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②我国近些年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这段历史。③目前有关托勒密王朝的很多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王权与神权的关系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国外学者在研究托勒密王朝的历史问题时涉及了托勒密王对神庙和祭司的管理情况。例如,塔恩在《希腊化文明》中非常简短地叙述了国王对宗教和祭司的管理与对其各方面权利的限制,④朱格特也在《马其顿帝国主义与东方的希腊化》中简略地介绍了托勒密国王对宗教、神庙和祭司的管理措施,⑤超万在《克娄巴特拉时代的埃及》一书里面专辟一章叙述了埃及的祭司与神庙的地位和国王对它们的管理情况。⑥国内外学者也都对托勒密王朝的祭司进行了研究,他们都强调了祭司集团在维系法老埃及的传统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注意到了祭司集团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中作为思想宣传工具的作用。⑦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在把托勒密王朝与法老埃及相比较的情况下深入分析祭司集团在托勒密王朝的实际政治地位,没有直接从国王与神庙和祭司的关系上深入分析王权与神权的关系,更没有剖析托勒密王朝与法老埃及的王权和神权关系存在重大差别的深层次原因。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研究角度的不同和史料的缺乏与零散造成的。有幸的是,笔者近年获得了几部非常重要的史料集,例如古尔德主编的《纸草选集》(第1、2卷)、奥斯丁编译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古代资料选译》、布尔斯坦编译的《从伊普苏斯战役到克娄巴特拉第七之死的希腊化时代》、巴格纳尔和德龙编译的《希腊化时代历史资料译本》,⑧它们都包含一些有关托勒密王朝宗教和王权问题的史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原始史料。
王权即“君主的权力”,这是该词最基本的涵义。⑨一般来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宣扬他们的统治权力是神所赋予的,所以把这种统治权力叫做神权”。这种定义把王权与神权统一起来了。事实上,本文的王权是指实行专制王权的托勒密王朝的国王的权力,主要是在探讨专制王权制度下的国王权力。
神权是针对王权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神权是伴随着王权的出现而产生的,“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君主才有了对神的需求,有了君主才有了统一的神,有了王权才有了神权。在古代君主制国家,神权与王权并不能简单地统一起来,二者既统一又对立。王权更强调国王的世俗权威,而神权则往往与宗教权威有关。具体言之,神权是神的权威或者宗教的权威,或者更进一步说,神权由宗教崇拜的组织机构或宗教仪式场所——神庙和宗教崇拜的组织者以及宗教仪式的执行者和解释者——最高祭司来体现。本文探讨的神权是君主制国家的君主借助神的权威宣传君权神授时出现的神庙和大祭司的权力。
古代埃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国王作为神和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实施王权,借助神庙祭司的宣传加强王权的合法性和威力,而神和祭司则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和生存甚至发展壮大的物质与权力的支持。然而,在法老埃及,王权与神权之间并非总是和谐统一的,而是经常发生斗争,甚至发生冲突。但到了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主要通过对近些年出版的文献史料的解读,从托勒密国王的人格神化和国王对宗教的控制两方面,考察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并通过与法老埃及的比较,分析这种关系得以产生的深刻原因。
一、托勒密国王人格的神化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病殁巴比伦,其部将为争夺帝国的领导权展开了角逐。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托勒密韬光养晦、出于“一鸟在手,胜于十鸟在林”的政治考虑,放弃了对帝国领导权的争夺,而是趁混乱之机,获得了统治埃及的权力。公元前323年,托勒密到达埃及以后,顺利打败了亚历山大大帝离开埃及时任命的总督,当上了埃及的总督,掌握了统治埃及的实际权力。公元前305年,托勒密称王,史称“托勒密第一”。自此埃及开始了希腊王朝时期。(11)
但是,就在托勒密继任总督掌握实权后,他很快注意到自己面临着很多困难,除了尽快恢复埃及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维护自己、王朝和埃及的安全、抵御外来入侵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埃及人的认可,如何确保统治的长久。他发现,要想在埃及长治久安,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接受埃及本土人的宗教信仰,必须使自己具有神的特性,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托勒密宣称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的继承人。在埃及人看来,正是亚历山大大帝赶走了曾使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波斯人,给他们带来了自由,“埃及祭司已经把他看作是神的儿子了”。(12)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后,马其顿人试图把其尸体运回马其顿,但托勒密半路拦截了送葬队伍,把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运往埃及安葬,这就等于宣布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合法继承人。其次,托勒密还大力宣传自己在赶走波斯人和为埃及本土人收复失地的功绩。公元前311年的一块“总督碑”上有这样一段铭文:“我,托勒密,总督,我(把自己)交给神荷鲁斯……;(我还)把帕和泰坡两地的女神潘太努特的领地布陀交还给(荷鲁斯);从今天开始直到永远,(我)拥有它(埃及)的所有村庄、城镇、居民和土地。”(13)
通过这样的宣传活动,到托勒密称王后,他已经成了埃及本土人心目中的神。埃及祭司以王衔的形式宣布了托勒密国王的神性。亚历山大大帝和托勒密第一都享有较正规的王衔。托勒密第二的王衔是:“荷鲁斯‘强健的年轻人’,两女神‘英勇的大人’,金荷鲁斯‘他的父亲使他在赞美声中出现’,上下埃及之王‘拉神(Re)的卡(Ka)的力量,阿蒙神的钟爱者’,拉之子‘托勒密’。”(14)根据埃及人的观念,“荷鲁斯、两女神、金荷鲁斯、上下埃及之王和拉之子”这5个王衔是埃及法老神性的标志和权威的象征。(15)自托勒密第三开始,王衔越来越复杂,其长度简直令人费解,即使在法老埃及最强盛时期也难以找到如此长的名字,例如托勒密第五的王衔:“荷鲁斯‘(在赞美声中)出现在他父亲的圣座上的年轻者’,两女神(他是)‘英勇的大人,他已经重建了两地并使可爱的土地完整,他的心对诸神是虔诚的’,金荷鲁斯‘他已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像普塔神一样的喜庆节日的主人和像拉神一样的君主’,上下埃及之王‘爱他神父的神的继承者,普塔的选择者,拉神的卡的力量,阿蒙神的活的形象’,拉之子‘托勒密,永生者,普塔神所钟爱的,他如神,仁慈的主人’。”(16)王衔特别强调了国王的神性,如“诸神的继承者”、“普塔神的选择者”等,这是法老埃及的法老和托勒密第一、第二的头衔中所没有的;王衔还强调了托勒密第五的重要贡献,如“他已经重建了两地并使可爱的土地完整”、“他已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等。从托勒密第六到托勒密第十二,国王的头衔构成有所发展,融入了一些新内容,例如“活着的阿匹斯(Apis)神牛的双胞胎兄弟”。克娄巴特拉第七的头衔仅由一个圈在王名圈内的荷鲁斯衔构成,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头衔。(17)荷鲁斯衔是5个王衔当中最早出现的,即使在王朝末期,王权式微的情况下,克娄巴特拉第七还能拥有这一头衔,这说明了托勒密王的神性基础之牢固,说明了托勒密王对人格神化的重视;但这种不完整的头衔也表明王朝末期的托勒密王逐渐失去了埃及本地祭司的支持。
托勒密国王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埃及神,从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期开始,他们还在有生之年与其王后一起享有特殊的神的称号和荣誉。(18)托勒密第一和他的妻子被称为“救主”,托勒密第二和他的妻子被称为“爱其姊妹之神”。托勒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分别被称为“善行者、施主”、“爱其(神)父之神”、“聪慧无误之神”、“爱其(神)母之神”,托勒密第七、第十四和克娄巴特拉第七也都被称为 “爱其(神)父之神”,等等。(19)
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在埃及变成的神不仅是法老时代那种令人敬畏的神,还是慈爱和受人尊崇的神,从而其地位更加不可侵犯和动摇。国王是王权制度的核心,是王权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国王人格得到神化,也就等于王权被神化,至少可以说王权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可以说,托勒密王朝的王权因国王人格的神化而与神权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表面上看,国王被称为“拉之子”,是太阳神拉的儿子,说明国王与神之间是一种父与子的关系,神高高在上,国王要对拉神这个“父亲”行孝顺服从之道,理论上,神权是永远高于王权的。宗教上,托勒密国王本人也是神,是荷鲁斯神、“爱其(神)父之神”、“聪慧无误之神”、“爱其(神)母之神”等等;政治中,也是最重要的,托勒密国王是“上下埃及之王”,就是说,托勒密国王才是真正掌管埃及的人世之神,埃及的一切归托勒密国王拥有。这样,埃及领土之内的神、神庙和祭司都要接受国王的安排。正是因为理论上托勒密国王为神,他们才可以控制神、神庙和祭司。那么,托勒密国王在实践中又是怎样控制神权的呢?
二、托勒密国王对宗教的控制
托勒密王朝的宗教在国王人格的神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国王并没有向宗教馈赠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是紧紧地掌控着宗教。
首先,托勒密国王在尊重传统宗教发展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崇拜形式。托勒密王朝允许埃及传统的多神崇拜,“从托勒密王朝统治早期,保持传统埃及宗教就是其根本宗教制度”。(20)同时,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托勒密第一建立了新的宗教——萨拉匹斯(Sarapis)崇拜,并把其作为官方宗教崇拜形式,这种崇拜形式获得了很大发展。(21)萨拉匹斯神是托勒密王朝的保护神,其崇拜中心在亚历山大城和孟菲斯地区,两地都有这一神的神庙,与此同时其神庙也遍及上、下埃及。萨拉匹斯神是埃及传统神和希腊神的认同合一,是一个男性人形神。古典作家塔西陀认为它起源于小亚细亚,原型是巴比伦的沙尔阿普希神(ar apsi,即水神恩基)。(22)现代学者则认为萨拉匹斯来自埃及神奥索拉匹斯(Osorapis),是奥西里斯神(Osiris)和阿匹斯神相结合的产物。奥西里斯神是古代埃及的冥府之神,阿匹斯神是孟菲斯地方的保护神。萨拉匹斯神在托勒密第一之前就已经存在。从本质上讲,萨拉匹斯含有死后再生、农业、生产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正与希腊神宙斯主宰世界、狄奥尼修斯神管理生产、哈德斯神管理冥界和医病的特点相吻合。(23)这个神的崇拜既满足了希腊马其顿移民的宗教情感,又符合埃及本土人的宗教观念。所以,托勒密王朝把这个神作为国家的保护神进行崇拜,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埃及的宗教发展方向。
其次,托勒密国王通过对神庙祭司的任命、召开神庙会议、派官员对神庙进行行政管理,掌握了神庙和祭司集团的命运。托勒密国王是宗教首脑。国王严格控制着神庙和祭司。每一位国王登基时都要任命一个属于自己的高级祭司。下面这则铭文就反映了这样的情况:“我去了国王的王室所在地,它位于‘伟大的绿海’(地中海)之滨,卡诺匹克支流的两边,它的名字是拉考提斯。上下埃及之王,神菲拉帕托尔·菲拉戴尔夫斯,年青的奥西里斯(托勒密第十二)离开他那具有生命和活力的宫殿,去了伊西斯神庙……,慷慨地向(女神)赠送大量贡物。当国王乘坐双轮马车离开伊西斯神庙时,他亲自停下双轮马车,把镶有金子和各种纯宝石的花冠放在我的头上,花冠上雕刻着国王的肖像。这样,我变成了他的祭司,而且他给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诺姆发出了一道敕令,说:‘我已经提升普塔神的高级祭司普森普泰斯,作我的宗教仪式的祭司,他可以从上下埃及的神庙中获得收入。’”(24)从理论上讲,国王不仅任命属于自己的高级祭司,全国的祭司都由国王任命,为国王服务。在一些文献中,我们发现祭司直接被称为“兄妹神(菲拉戴尔夫斯和阿尔茜诺)”的祭司、“仁慈者”神的祭司等,(25)也就是说,祭司是国王的。
至少到托勒密第五时,祭司集团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国王任主席。(26)召开会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强化国王作为神庙或者宗教首领的事实,一是了解神庙和祭司的情况,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托勒密国王对神庙的控制,除了依靠自己在登基时任命的大祭司,还要依靠神庙的各级祭司和各级地方官吏。他们都代替国王管理具体的宗教事务,比如地方警察负责神庙的安全,村书吏和村长负责神庙的经济收支,而诺姆(州)的代总督则代表国王对所辖诺姆内所有神庙实行行政监督和管理。(27)
此外,托勒密国王还通过主持重大宗教仪式和颁布一些规范宗教活动的敕令直接掌管宗教。托勒密国王亲自主持某些重大的宗教仪式。有一篇文献记录了托勒密第二主持的纪念托勒密第一的宗教仪式——“大行进队伍”(GreatProcession),文献记载到:国王走在这个仪式队伍的中间,前面是诸多神祇的雕像,由祭司们抬着,其中托勒密第一和其王后的雕像最为突出,他们是神“索塔尔”(“救主”),国王后面是众大臣、地方代表、地方神庙的祭司、米利都等附属国的代表以及这些大臣、代表、祭司们奉献的祭品。队伍非常庞大,全亚历山大城的人们都加入其中,走在队伍的后面,后者忙于为行进队伍和祭祀活动做各种准备,例如准备祭品、准备祭祀场所等。之后,祭祀活动在庄严的气氛中开始,托勒密第二作为国王、神以及最高祭司主持仪式的整个过程。(28)
托勒密国王对神庙的控制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就连人们参加宗教仪式的行为,都要受到国王的规定。例如,大约公元前267年,托勒密第二对那些向阿尔茜诺·菲拉戴尔夫斯献祭的人们,给出了这样的命令:“(关于那些)希望给阿尔茜诺·菲拉戴尔夫斯献祭的人们,让他们在自己的受捐者前面或他们的房子上或沿卡奈夫洛斯公路两边献祭。让所有人献祭一只禽,(或者)献祭其希望献祭的(任何事物),包括公山羊和母山羊。并且,人们要用沙子建筑祭坛;但如果一些人用砖建筑了祭坛,那么他们要把沙子铺在上面……”(29)再如,公元前3世纪中期,国王托勒密第四对普通人参加狄奥尼修斯宗教节日的时间作了如下规定:“那些在内地执行狄奥尼修斯仪式的人们,应该向下航行至亚历山大城,在亚历山大城和诺克拉底斯城之间的那些人在法令颁布日期的10天之内、那些远于诺克拉底斯城的人们在20天之内到亚历山大城,应在他们到达亚历山大城的3天内到登记处的阿里斯托布鲁斯面前登记,应立即宣布他们从什么人那里获得了参加神圣仪式的授权,前推三代,应交上密封好的圣书,在每一本圣书上记上他自己的名字。”(30)
从现存文献中,我们所发现的都是国王对宗教事务进行处理或者对宗教祭司们任命以及发号施令的文件,没有发现宗教祭司干预世俗政权的事例。无论地方官僚(如警察、代总督和村长等),还是宗教祭司,他们都是在国王的许可下处理宗教事务,至少都是按国王的意志办事。也就是说,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对宗教祭司集团和宗教事务拥有绝对权力,神庙和祭司集团根本不敢奢望从国王那里得到更多的馈赠和权利,祭司集团已失去了像法老埃及时期那样的独立性,处处受到国王的利用与限制,未能与世俗政权发生严重冲突,神庙和祭司集团是完全为世俗政权服务的工具。从而托勒密王朝的王权与神权完全是一边倒的关系,王权是主角,神权只是为王权服务的配角。
三、托勒密国王成功控制神权的原因
法老埃及的神权与王权之间就不是和谐一致的,处于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状态,神权经常彰显,王权时常受到神权的影响,经常受到宗教祭司集团的制约。(31)新王国时期埃赫那吞宗教改革便是王权与神权斗争的产物。但在托勒密王朝,国王有效地利用了宗教,掌控着宗教的发展方向,使宗教不能觊觎王权或干涉世俗政权。为什么到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埃及的王权与神权关系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或者说,为什么托勒密王朝的王权能够成功地控制神权呢?这恐怕与托勒密王朝的经济政策、政治导向、等级状况和统治者的文化背景等都有重要关系。
首先,我们从托勒密王朝的经济政策上寻找根源。托勒密王朝沿用法老时期的土地制度,但是更加强化了国王对土地的绝对权力。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整个土地属于国王,大批土地由国王直接掌握和管理。”(32)他把全国土地分为两大类:即由王室直接经营的“王田”和授予神庙贵族、各级官员和士兵的“授田”。(33)王田大部分由王田农夫耕种。王田农夫以契约的形式、以实物地租的方式租种王室土地,地契随时更改,还必须向国王缴纳一定量的税务。公元前113年的一份文献就反映了村书吏美奇斯计算村庄实物地租的情况。王田农夫被严格管束在村社内,不得自由迁徙,其劳动受到严格监管。王田农夫从国王那里领取种子、农具和牲畜,其生产的全过程——从种植到收获、加工,都要受到国王委派的官吏的监督与安排。授田上的劳动者是税收的主要生产者,因而享有一定的特权。(34)但是,他们也同样处于托勒密国王的严格控制下,而且他们还要在筑堤和建筑水渠时履行义务劳动。
神庙土地以同样的方式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并受到盘剥,但税收用以维持神庙的存在和发展。神庙贵族所掌握的土地数量显然有限,因为大部分土地被分配给军人。(35)虽然我们不知道军人拥有土地的总量是多少,但我们可以做一推测。据阿庇安记载,“托勒密第二统治时,税收是充足的,可以支持巨大的军事建设,包括240000名步兵和骑兵,300只战象和3500只战船。”(36)这样的数目并不算夸张。据狄奥多拉斯记载,克娄巴特拉第七统治时,埃及的人口大约700万,这一人口统计数字是较为准确的。因为,埃及国土面积大约1002000平方公里,(37)除去沙漠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10人的比率还是比较适合当时埃及的情况的。当然,托勒密第二的这支军队,显然包括全国所有的军人,因为“希腊化国王们在彼此战争时可能领导的军队数目在60000到80000之间。”(38)这些军人即使不全是拥有土地的殖民兵(cleruch),(39)也有大部分是殖民兵。按希罗多德的记载,舍易斯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一前525年)的法老把一些土地分给埃及士兵,每个士兵获得12阿鲁拉(aroura)的份地,无论他们是否正在服役,这些土地并不是由同样的一些人一直耕种下去,而是交替着耕种的。(40)托勒密国王们在继承舍易斯埃及军事殖民政策的同时,其政策还有所发展。托勒密王朝规定:和平时期把职业军和雇佣军安排在特定的区域,按军衔高低,分给他们不等份额的土地,由他们自己或雇用埃及本土人开垦和耕种,扣除税收之后的收入作为他们的军饷,他们可以耕种这块土地直到去世,是否可以继续由儿子继承,要由国王做出决定。例如公元前239年12月—前238年1月,一份关于军事殖民的文件,这样写道:“下面列出的骑兵已经死了,因此为国王取回他们的份地。”(41)虽然我们不知道每个军人的份地是多少,但这块份地足可以令其养家糊口,甚至可以雇人耕种,可见其面积并不是很小。我们从文献中可以发现士兵最少也可以拥有7到10阿鲁拉的土地,多者可达100阿鲁拉。可见,军人的土地占去了授田的很大一部分。另外,官员的授田数量也比较可观,最低级的村书吏可以获得10阿鲁拉的土地,(42)而托勒密第二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更是拥有相当多的土地。从而,我们可以断定托勒密王朝的神庙拥有的土地很少,如果再分摊到全国的每个神庙,那么其土地数量根本无法与王田相比,甚至都无法与军人和官员的授田相比。因此,“托勒密时期的祭司是埃及3个主要的土地占有者之一”(43)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托勒密国王对产业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托勒密王朝的产业部门已较多,如榨油业、纺织业、盐业、玻璃制造业、纸草制造业、采矿业、酿酒、制陶等等。在这些产业中,榨油业的专营是托勒密国王最主要的产业专营项目。“一些产业分支只由国家来操作。蔬菜油的准备完全是这样的。所有的制造厂和原材料都绝对属于国家。”(44)从种植原油植物的种子的领取、种植、加工到卖出的整个过程都被国家严格地控制着。制油工厂的工人虽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但也不允许在榨油的季节离开工厂,以前存在的私人油坊,现在已被禁止。神庙也仅仅给两个月的时间榨油,油的价格由政府制定,是固定的,而且必须由批发商出卖。(45)公元前259年一份有关托勒密第二时期油专营的法令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46)第二大专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在国家的严格监督和控制之下,每个工厂的生产必须得到国王的批准。(47)祭司也被允许生产一定的纺织品,但必须缴纳大量的亚麻给国王,以满足出口的需要。(48)其他的垄断性行业还有盐、“那特仑”和啤酒制造、采矿等。(49)国王对这些行业征税,(50)还规定工业品的价格。(51)神庙在产业中的活动十分有限,而且备受限制,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托勒密王朝进出口贸易获得了发展。亚历山大城是进出口的重要基地。出口贸易都掌握在亚历山大城的贵族和官僚手中。几乎所有的进口货物也由亚历山大城的王室成员操纵。(52)贸易领域几乎见不到祭司的身影。可见,在经济政策上,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严格限制神庙的土地,限制祭司参与经济生产和各种贸易活动,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神庙和祭司集团的发展与强大。
其次,从政治导向上来看,托勒密国王有意识地从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上限制祭司集团的发展。在法老埃及,法老借助宗教宣传加强自己的神性,加强统治基础,祭司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积极宣传国王的神性;作为回报,法老对祭司和神庙给予大大嘉赏,从而祭司集团的权势逐渐加强。埃及考古学家阿哈默德·费克里在论及第二十王朝时期阿蒙神和僧侣积累财富和权力时,说道:从哈里斯大纸草上,我们读到阿蒙·拉神的大祭司长,接受了拉美西斯第三的赠与之后,“拥有埃及全部可耕地的1/10,有5群牲畜,数目不少于421000头,还有68500名奴隶在他的田地上做工,各处土地和沃土上都有他的花园和果园。另外,他还占有努比亚的金矿,还有从叙利亚9个城市得到的收入。如果算上虔诚的百姓经常施舍给神庙的供奉,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那些僧侣的权利远远超过国内任何人,包括国王在内。”(53)显然,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费克里教授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能责备拉美西斯第三,因为我们记得在他之前的世代,所有的国王都给阿蒙神纳贡,他们没有一个人试想着从阿蒙神的财产里拿走一点,而所有的人,除了埃赫那吞外,都曾想以赠物使它更富有。(54)虽然埃及法老的主观意愿不一定是“想以赠物使它(阿蒙神庙)更富有”,但从客观上确实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神庙和祭司集团拥有了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就有了干涉世俗政权的资本。而各方面的开支、多方面的经济消耗、国内外政治斗争等都使法老的经济实力、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日渐受到削弱,当中央集权衰弱,王权出现危机时,宗教祭司集团便成为王权的最大敌手,尤其可以在经济上对王权施加压力,进而左右政权。在托勒密王朝,也有国王向神庙馈赠财产的情况。例如,托勒密第一曾向埃及神庙捐献了50塔兰特,作为一只阿匹斯圣牛的葬仪费用,托勒密第二曾赠与埃及各神庙75万德本的白银,托勒密第四完成了埃德福神庙的建筑,并在戴尔·美蒂那建立了神庙。(55)但我们未发现任何国王曾向神庙奉献过土地,甚至这里国王奉献白银和建筑神庙也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支持多神崇拜,出于对埃及本土人宗教情感的维护而已。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托勒密国王有意识地进行的,他们必定从法老埃及的历史中汲取了经验。托勒密国王不向神庙和祭司集团馈赠土地和大批量的财产,这就消除了宗教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法老埃及,法老允许部分祭司,尤其是大祭司参加行政管理,甚至任命他们担任某些重要官职。例如,在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第二统治第46年的一次审判中,10名审判官中有9人是神庙僧侣。(56)又如,第二十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第十一统治时期,一个名叫荷里霍尔的人担任了阿蒙高僧职务,到拉美西斯第十一统治末期,他已经作为总督和将军而掌握了上埃及和努比亚的实权。(57)再如,第二十三王朝后期,赫尔摩坡里斯的地方官尼姆赫特就是神庙高僧,他采用了国王的称号并宣布独立。(58)祭司集团掌握部分世俗政权,这就为他们干涉朝政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这也是法老埃及神权可以与王权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托勒密王朝,国王没有给予任何祭司参政的机会,就连国王登基时任命的高级祭司也必须听命于国王,而且不能参与行政事务,这就从行政上把祭司们排除在外了,消除了他们在行政上影响王权的可能性。
再者,阶级和等级状况也决定了托勒密王朝的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法老埃及只有阶级没有等级,统治阶级是以法老为首的大批官僚和祭司集团,而被统治阶级是广大埃及民众。祭司集团是法老埃及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就使他们完全可以加入国家的行政管理行列,进而觊觎和干涉王权。托勒密王朝的等级结构与法老埃及大不相同。在托勒密王朝,统治阶级是希腊马其顿人,他们也是社会的第一等级,享有各种特权;被统治阶级是埃及本土人和其他外来移民,他们是第二等级。在第二等级中,即在被统治阶级中,还有一个埃及本土祭司和地方贵族阶层,他们充当了希腊马其顿人统治埃及的工具,当然也享有一定的权力,社会地位相较于普通埃及本土人要高一些,他们是第二等级中的上层。第二等级的下层,即社会的最底层,是普通埃及本土人和其他外来移民。不可否认,“有一些高级祭司和几个独特的埃及人在行政机构中获得了重要职位,他们形成了一个埃及本土人官僚阶层,但在主要政治领域,埃及人的社会职位比希腊移民低。他们只是王室土地的技工和佃农,即使他们获得了份地或‘私人’土地,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通常也比希腊人的少。”(59)“埃及祭司仍执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庆祝重大节日,而埃及的农民仍然开发他们的土地,对赋予了他们尼罗河洪水的神祇感恩至深。但整体上,埃及人已从领主降到了低级劳动者,降到了社会第二等级,在它之上是一个希腊人阶层。”(60)一部分埃及本土人可以借助财富和知识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等级,也就是说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埃及人可以上升为第二等级的上层,但必须接受教育,了解希腊文化。比如马涅陀,他显然既懂希腊文又懂埃及文,而且对两种语言都很精通,因而才获得重用。而埃及人中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并不多,只有那些社会上层人士和富有者才有这样的机会。因而广大的下层农民仍然生活在他们的传统世界里,保持他们古老的传统和生活模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制定契约。(61)由于这种等级关系,埃及本土祭司注定不能掌握大权,不能左右政权。
马其顿和希腊移民占据统治上层,埃及本土人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二等级。从阶级上来说,祭司集团作为有产者,作为希腊马其顿人的联盟,具有一定的权威和地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始终不能掌握主要政治权力,始终处于希腊和马其顿人的控制之下,即使王权势力衰弱了,他们也因经济、权力和地位的弱势而不能干涉政权。可以说,在国王与埃及祭司集团之间,是一个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统治阶级和第一等级,他们有效地隔断了神权发展的道路。
此外,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托勒密国王与埃及本土人对神的认识不同。“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神和人之间并不存在多大差别。”(62)在希腊人看来,神具有人的特征,神并不是万能的,有胜利也有失败,甚至可以被镇压。例如,《荷马史诗》中的众神一面通过现实中的英雄进行战斗,从中找到胜负之分;一方面亲自参加凡人的战斗,帮助一方打败另一方,甚至有时两个神灵直接兵刃相见,一见高低;每次战斗都有胜有负。史诗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神的认识,而《荷马史诗》决非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产物,所以它体现的是希腊人们对神的认识。这种文化培养了马其顿人对神的基本看法,不会像埃及本土人那样虔诚地相信神的万能和至高权威,而是认为埃及的神与希腊的神有相似性,(63)认为他们的统治并不是神赋予的,而是自己依靠武力夺取的,并认为神、神庙和祭司只是帮助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托勒密国王对神的这种认识使他们到埃及进行统治时,只是赤裸裸地把埃及传统的宗教作为统治工具,从意识深处拒绝把更多的权力让渡给高级祭司或祭司集团,更不愿意看到神庙势力的发展。这种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使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埃及本土人的支持。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国王克娄巴特拉第七的头衔只有一个荷鲁斯衔,这似乎表明埃及祭司不再像王朝前期那样支持托勒密王了。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古代埃及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神权与王权紧密关联。法老埃及的神权与王权处于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状态。在文明独立发展的历史时期,当神权的势力彰显时,王权受到神权的牵制。神庙势力的强大体现在法老必须给予神庙和祭司集团大面积的土地和大量的经济利益以及一定的政治权力。到了托勒密王朝时,这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外族国王以武力掌控了埃及本土宗教,对宗教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宗教只是武力征服本土的国王进行统治的工具。依附于王权的神权实际上是王权的婢女。托勒密国王作为外族统治者始终从经济、政治等方面严格限制着本土祭司集团和神庙的发展壮大。归根结底,宗教是为经济和政治服务的上层建筑,由于历史原因和王权神授的宗教信仰,埃及神权在本土王朝统治期间成为王权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因此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利益。在希腊化外族统治期间,王权的主要支撑点是武力和希腊化的贵族及希腊宗教和思想,被统治阶级的埃及本土宗教并不完全和谐于统治阶级外来宗教。这样,由于托勒密时期的王权与神权在阶级、民族和文明背景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王权神授的庄严外衣下遮盖着希腊人的王权和本土的传统神权之间的赤裸裸的利用关系。这也是托勒密王朝被罗马人战败后,及后来统治埃及的拜占庭人被本土阿拉伯人战败后迅速失去埃及人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8年3月26日]
注释:
①一般来说,古代埃及历史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国家形成之前的埃及(公元前3100年之前)、法老埃及(公元前3100—前332年)、马其顿征服(公元前332—前323年)、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前30年)和罗马埃及(公元前30—公元641年)。关于托勒埃及的起始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始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参见I. Shaw,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82;刘文鹏:《埃及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页,有人认为始于公元前321年亚历山大城竣工,参见陈恒:《关于希腊化时代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45页,也有人认为始于公元前305年托勒密称法老,参见D. B. Redfor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Vol.Ⅱ,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76。本文以为,托勒密埃及亦指托勒密王朝时代,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公元前323—前305年,托勒密以埃及总督的身份统治埃及,一是公元前305年—前30年托勒密王朝时期。
②“布歇—勒克莱尔的《托勒密·拉格斯王朝史》,参见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50页注释3;Edwyn Bevan, A History of Egypt under the Ptolemaic Dynasty, London: Methuen & Co.Ltd.,1927.
③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78-629页。
④W. Tam and G. F. Griffith,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52, p. 201.
⑤P. Jouguet, Macedonian Imperialism and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307-308.
⑥M. Chauveau, Egypt in the Age of Cleopatr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0-133.
⑦参见J. H. Johnson, "The Role of the Egyptian Priesthood in Ptolemaic Egypt", in L. H. Lesko ed., Egypt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Richard A. Parker Presente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8th Birthday December 10, 1983, Hanover, New Hampshire &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6, pp. 70-84; D. J. Thompson, "The High Priests of Memphis under Ptolemaic Rule", in M. Beard and J. North ed., Pagan Priest: Religion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Duckworth, 1990,pp.95-116;苏联社会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330页;颜海英:《希腊化时期埃及祭司集团的社会地位》,《中国博士后社会科学前沿问题论集》,北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58-271页;李模:《诸神的仆人们——古代埃及祭司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年。
⑧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 I, Vol. II, trans, by A. S. Hunt and C.G. Edgar,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1934; M. M. Austine,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S. M. Burstein, ed.,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Ipsos to the Death of Kleopatra 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R. S. Bagnall and P. Derow, ed., 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Oxford: Blachwell publishers, 2004.
⑨王权亦被视为一种政体。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政治学》中把158个希腊城邦以及希腊世界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体进行横向比较而区分了三种正常政体和三种变态政体:王制(basileus)和僭主政治,贵族政体和寡头政体,共和政体和民主政体,(Arist., Pol., 1279a25-1279b10, in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 by H. Rackha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1945,pp.204-207)并把王制区分为5种形式,大多处于两个极端形式——“即大权独揽的王制和斯巴达式的王制”——范围内。(Arist., Pol., 1285a1, 1285b20-35, in Aristotle, Politics,pp.246-247,252-255)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5种王制实际上包括了王制一词从军事首长到专制君主的各种内涵,包括了到亚里士多德写作《政治学》之时已知的王权和专制主义在内的各种王制。当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提出专制主义这种政体,因为当时还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专制主义这个词,他的5种王制之中确实含有专制主义这种王制形式而已。但是,亚里士多德论述王制的根本目的在于论证这种制度是否是正确政体,是否适合城邦,并未具体分析其历史发展过程,而是对他所知和所见之王制进行静态的分析。本文认为王制包括王权和专制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有一个从王权到专制主义的演变过程。一般来说,王权还不成熟,国王的权威受到多种力量或势力集团的限制。专制主义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王的权力已较为完善,具备了专制君主的特质,很少受到或不受其他势力集团或力量的限制。当然,并不是说王权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专制主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王权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上有所不同,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经过王权直接进入专制主义;有些则在王权之后直接进入了民主制或共和制国家,没有经历专制主义;有些则在王权之后逐渐进入了专制主义阶段。关于王权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的王制的关系,本文作者还将另行撰文进行深入探讨。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页。
(11)无论希腊城邦人民和马其顿人的民族认同是什么,但从语言、习俗和宗教崇拜等方面看,马其顿人与希腊城邦人民具有共同之处,从而一般来说,马其顿人仍可算作希腊人。
(12)H. I. Bell,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31.
(13)A. K. Bowman, Egypt after the Pharaohs 332BC-AD642 from Alexander to the Arab Conqu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1.
(14)M. Chauveau, Egypt in the Age of Cleopatra, p. 45.
(15)J. p. Allen, Middle Egypti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4-66.
(16)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 374.
(17)M. Chauveau, Egypt in the Age of Cleopatra, p. 46.
(18)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II, pp. 191,243.
(19)M. Chauveau, Egypt in the Age of Cleopatra, pp. 6-27.
(20)A. K. Bowman, Egypt after the Pharaohs 332BC-AD642 from Alexander to the Arab Conquest, p. 169.
(21)H. I. Bell,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 pp. 38-39.
(22)Tac., Hist., IV. 83-84, in Tacitus, The Histories, The Annals, Vol. II, trans, by C.H. Moo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62-167.
(23)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619页。
(24)M. Chauveau, Egypt in the Age of Cleopatra, p. 48.
(25)奥斯丁:《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第366、367页。
(26)P. Jouguet, Macedonian Imperialism and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East, p. 300.
(27)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 367.
(28)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p. 361-362.
(29)S. M. Burstein,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Ipsos to the Death of Kleopatra VII, p. 119.
(30)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II, p. 57.
(31)关于法老埃及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可参见刘文鹏:《埃及学文集》,第223页。刘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只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般性概括,而没有展开,实际上这个问题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32)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II, p. xxi.
(33)W. Tarn and G. T. Griffith,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pp. 187-189.
(34)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II, pp. 515、35-39、69、73.
(35)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II, pp. 69-75、12.
(36)Appian,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reface10.
(37)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11页。
(38)J. Boardman, J. Greffin and O. Murray, Greec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20.
(39)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p. 453-454.
(40)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II.168。
(41)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 426.
(42)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II, pp. 71、237、393.
(43)B. G. Trigger, Ancient Egypt: A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01.
(44)F. W. Walbank, et al.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p. 135.
(45)H. I. Bell,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 p. 57; 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p.401-404.
(46)R. S. Bagnall and P. Derow, ed., 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pp. 181-195.
(47)F. W. Walbank, et al.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II, p. 136.
(48)H. I. Bell,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 p. 49.
(49)M. Rostovtzeff, Social &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308-313.
(50)F. W. Walbank, et al.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II, p. 136.
(51)R. S. Bagnall and P. Derow, ed., 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p. 197.
(52)F.W. Walbank, et al.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II, pp. 134、135.
(53)阿·费克里著,高望之等译:《埃及古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53页。关于哈里斯大纸草,可参见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Ⅳ, New York,1962, pp.87-206;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集·上古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1-30页。哈里斯大纸草详细记录了古代埃及第二十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第三向阿蒙神庙、太阳神拉神庙和普塔神庙及其祭司们馈赠大量土地和物品的统计数字。
(54)阿·费克里著,高望之等译:《埃及古代史》第153页。
(55)A. Dodson and D. Hilton, The Complete Royal Famili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p. 264.
(56)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II, p. 224.
(57)N. Grimal,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2, pp. 291-292.
(58)K. A. Kitchen,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 New York: Philips Publishing, 1973, p. 361.
(59)H. I. Bell,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 pp. 36.
(60)L. Casson, 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Egyp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7.
(61)H. I. Bell,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 pp. 42-43.
(62)J. H. 布雷斯特德著,李静新译:《文明的征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325页。
(63)阿夫季拉的海卡泰俄斯认为希腊人将埃及最有名的神祇据为己有。Diodorus, Library of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I.24.1.
转自《古代文明》(长春)2008年4期第18~27页
责任编辑:刘悦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上一篇: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
下一篇:论都铎英国的货币管制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